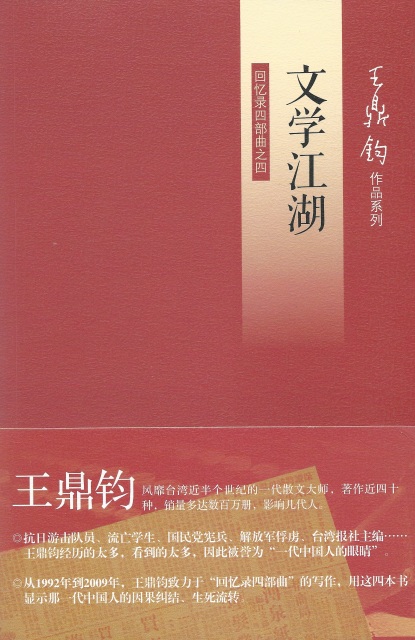文學江湖 (簡體字版)
SKU:
$0.00
Unavailable
per item
出版發行: 北京三聯書店
出版年: 2013 (2013 年1月初版)
總頁數: 354
ISBN 978-7-108-04219-4
内容简介 (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四):
王鼎钧1949年漂流到台北,卖文为生,先后进入广播、报纸、电视等媒体,主持文字工作。那年代台湾处于权威统治的高压之下,文字狱连续发生,新闻媒体又属于敏感事业,人人自危,王鼎钧凭他忧患磨练而生的智慧,勤苦学习而得的文学技巧,和当时的特务人员对奕,渡过一个又一个险滩,奇趣横生。那时台湾有「民主自由或集权专政」的论争,好学深思的王鼎钧置身其中,亦有深刻的体验与精采的记事。王鼎钧说他毕竟是一个作家,取材偏重文学艺术的坎坷发展,他自己如何由文艺青年到散文名家,也在书中留下成长的记录,极有参考价值。凡此种种,显出此书别具一格,与众不同,至于诗笔的感性,史笔的理性,渔樵闲话一般的趣味性,使文学评论家纷纷予以很高的评价。
出版年: 2013 (2013 年1月初版)
總頁數: 354
ISBN 978-7-108-04219-4
内容简介 (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四):
王鼎钧1949年漂流到台北,卖文为生,先后进入广播、报纸、电视等媒体,主持文字工作。那年代台湾处于权威统治的高压之下,文字狱连续发生,新闻媒体又属于敏感事业,人人自危,王鼎钧凭他忧患磨练而生的智慧,勤苦学习而得的文学技巧,和当时的特务人员对奕,渡过一个又一个险滩,奇趣横生。那时台湾有「民主自由或集权专政」的论争,好学深思的王鼎钧置身其中,亦有深刻的体验与精采的记事。王鼎钧说他毕竟是一个作家,取材偏重文学艺术的坎坷发展,他自己如何由文艺青年到散文名家,也在书中留下成长的记录,极有参考价值。凡此种种,显出此书别具一格,与众不同,至于诗笔的感性,史笔的理性,渔樵闲话一般的趣味性,使文学评论家纷纷予以很高的评价。
Sold Out
选文试读:(一)匪谍是怎样做成的
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湾宝岛,七月,澎湖即发生「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」冤案,那是对我的当头棒喝,也是对所有的外省人一个下马威。当 年中共席捲大陆,人心浮动,蒋介石自称「我无死所」,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,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, 一件「二二八」事件慑伏了本省人,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伏了外省人,就这个意义来说,两案可以相提并论。
烟台联中冤案尤其使山东人痛苦,历经五○年代、六○年代进入七○年代,山东人一律「失语」,和本省人之于「二二八」相同。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「八 千子弟」中的一个分子,我们也从不忍拿这段历史做谈话的材料。有一位山东籍的小说家对我说过,他几次想把冤案经过写成小说,只是念及「身家性命」无法落 笔,「每一次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无耻。」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。
编剧家赵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学生,他去世后,编剧家张文祥写文章悼念,谈到当年在澎湖被迫入伍,常有同学半夜失踪,「早晨起床时只见鞋子」,那 些都是强迫入伍后不甘心认命的学生,班长半夜把他装进麻袋丢进大海。这是我最早读到的记述。小说家张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,他的中篇小说〈海兮〉以山东流 亡学生在澎湖的遭遇为背景,奔放沉痛,「除了人名地名」以外,直言不讳。然后我读到周绍贤〈澎湖冤案始末〉、傅维宁〈一桩待雪的冤案〉、李春序 〈傅文沉冤待雪读后〉,直到〈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〉、张敏之夫人回忆录〈十字架上的校长〉,连人名地名都齐备了。
可怜往事从头说:内战后期,国军节节败退,山东流亡学生一万多人奔到广州,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出面交涉,把这些青年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。 当时约定,让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,十七岁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,天下有事投入战场,天下无事升班升学。当时,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澎湖当家作主的陈诚都批准这样安排。
一九四九年六月,学生分两批运往澎湖, 登轮者近八千人, 后来号称八千子弟。七月十三日,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,把年满十六岁的学生,连同年龄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「标准」的学生,一律编入步兵团。学生举手呼 喊「要读书不要当兵」,士兵上前举起刺刀刺伤了两个学生,司令台前一片鲜血,另有士兵开枪射击,几个学生当场中弹。三十年后,我读到当年一位流亡学生的追述,他说枪声响起时,广场中几千学生对着国旗跪下来。这位作者使用「汴桥」做笔名,使我想起「汴水流,泗水流……恨到归时方始休」,可怜的孩子,他们捨死忘生追赶这面国旗,国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块布。
编兵一幕,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监督进行。流亡学校的总校长张敏之当面抗争,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动学生造反。李振清虽然是个大老粗,到底行军打仗升到将军,总学会了几手兵不厌诈,他居然对学生说:「你们都是我花钱买来当兵的!一个兵三块银元!」他这句话本来想分化学生和校长的关係,殊不知把 张敏之校长逼上十字架,当时学生六神无主,容易轻信谣言,这就是群众的弱点,英雄的悲哀,自来操纵群众玩弄群众的人才可以得到现实利益!为他们真诚服务却要忧谗畏讥。张敏之是个烈士,「烈士殉名」,他为了证明人格清白,粉身碎骨都不顾,只有与李振清公开决裂,决裂到底。
张敏之身陷澎湖,托人带信给台北的秦德纯,揭发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。咳,张校长虽然与中共斗争多年,竟不知道如何隐藏夹带一封密函,带信使者在澎湖码头上船的时候,卫兵从他口袋裡搜出信来,没收了。张敏之又派烟台联合中学的另一位校长邹鑑到台北求救,邹校长虽然也有与中共斗争的经验,沿途竟没有和「假想敌」捉迷藏,车到台中就被捕了。
最后,张敏之以他惊人的毅力,促使山东省政府派大员视察流亡学生安置的情形,教育厅长徐轶千是个好样的,他会同教育部人士来到澎湖。李振清矢口否认强迫未成年的学生入伍,徐厅长请李振清集合编入军伍的学生见面,李无法拒绝,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带到海边拾贝壳。徐轶千告诉参加大集合的学生, 「凡是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学生站出来,回到学校去读书!」队伍中虽然还有幼年兵,谁也不敢出头乱动。张敏之动了感情,他问学生: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读书吗? 现在为什麽不站出来?徐厅长在这裡,教育部的长官也在这裡,你们怕什麽?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,你们错过了这个机会,再也没有下一次了!行列中有十几个孩子 受到鼓励,这才冒险出列。李振清的谎言拆穿了。后来办案人员对张敏之罗织罪名,把这件事说成煽动学生意图製造暴乱,张校长有一把摺扇,他在扇上亲笔题字, 写的是「穷则独搧其身,达则兼搧天下」,这两句题词也成了「煽动」的证据。
徐轶千对张敏之说:「救出来一个算一个,事已至此,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!」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,于是着手「做案」,这个「做」字是肃谍专家的内部术语,他们常说某一个案子「做」得漂亮,某一个案子没有「做」好。做案如做文章,先要立意,那就是烟臺联中有一个庞大的匪谍组织,鼓动山东流亡学生破坏建军。立意之后蒐集材料,蒐集材料由下层着手,下层人员容易屈服。那时候办「匪谍」大案都是自下而上,一层一层株连。
做案如作文,有了材料便要布局。
办案人员逮捕了一百多个学生(有数字说涉案师生共一百零五人)疲劳审问,从中选出可用的讯息,使这些讯息发酵、变质、走味,成为罪行。办案人员锁定 其中五个学生,按照各人的才能、仪表、性格,强迫他们分担罪名,那作文成绩优良的,负责为中共作文字宣传;那强壮率直的,参与中共指挥的暴动;那文弱的, 觉悟悔改自动招供。于是这五个学生都成了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分团长。
每一个分团当然都有团员,五个分团长自己思量谁可以做他的团员,如果实在想不出来,办案人员手中有「情报资料」,可以提供名单,证据呢,那时办「匪 谍」,只要有人在办案人员写好的供词上盖下指纹,就是铁证如山。这麽大的一个组织,单凭五个中学生当然玩不转,他们必然有领导,于是张敏之成了中共胶东区执行委员,邹鑑成了中共烟台区市党部委员兼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主任。
办案人员何以能够心想事成呢?唯一的法术是酷刑,所以审判「匪谍」一定要用军事法庭祕密进行。澎湖军方办案人员花了四十天功夫,使用九种酷刑,像神创造天地一样,他说要有什麽就有了什麽。最后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,判定两位校长(张敏之、邹鑑)五名学生(刘永祥、张世能、谭茂基、明同乐、王光耀) 共同意图以非法方式颠复政府,各处死刑及褫夺公权终身。这一年, 张敏之四十三岁,邹鑑三十八岁。同案还有六十多名学生,押回澎湖以「新生队」名义管训,这些学生每人拿着一张油印的誓词照本宣读,声明脱离他从未加入过的 中共组织,宣誓仪式拍成新闻片,全省各大戏院放映,一生在矮簷下低头。当时保安司令是陈诚,副司令是彭孟缉。
那时候,军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,五千多名入伍的学生从此与世隔绝。还有两千四百多名学生(女生和十六岁以下的孩子),李振清总算为他们成立了一所子弟学校,继续施教,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。下一步,教育部在台中员林成立实验中学,使这些学生离开澎湖。
我是后知后觉,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凑出整个案情。我也曾是流亡学生,高堂老母寿终时不知我流落何处,我常常思念澎湖这一群流亡学生的生死祸福,如 同亲身感受。有一天我忽然触类旁通,「烟台联中匪谍案」不是司法产品,它是艺术产品,所有的材料都是「真」的,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却是「假」的,因为 「假」,所以能达到邪恶的目的,因为「真」,所以「读者」坠入其中不觉得假。狱成三年之后,江苏籍的国大代表谈明华先生有机会面见蒋介石总统,他义薄云天,代替他所了解、所佩服的张敏之申冤,蒋派张公度调查,张公度调阅案卷,结论是一切合法,没有破绽!酷刑之下,人人甘愿配合办事人员的构想,给自己捏造 一个身分,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分,有了身分自然有行为,各人再捏造行为,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,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,这个结构有在内在的逻辑,互补互依,自给自足。
今天谈论当年的「白色恐怖」应该分成两个层次:有人真的触犯了当时的禁令和法律,虽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当的,当时执法者和他们的上司还可以採取「纯法律观点」原谅自己,另外一个层次,像张敏之和邹鑑,他们并未触法(即使是恶法!),他们是教育家,为国家教育保护下一代,他们是国民党党员,尽力实现党的理想,那些国民政府的大员、国民党的权要,居然把这样的人杀了!虽有家属的申诉状,山东大老裴鸣宇的辨冤书,监察委员崔唯吾的保证书,一概置之不顾,他对自己的良心和子孙如何交代?我一直不能理解。难道他们是把这样的案子当做艺术品来欣赏?艺术欣赏的态度是不求甚解,别有会心,批准死刑犹如在节目单上圈选一个戏码,完全没有「绕室徬徨掷笔三歎」的必要。
他们当时杀人毫不迟疑,真相大白时又坚决拒绝为受害人平反。说到平反,冤案发生时,山东省主席秦德纯贵为国防部次长,邹鑑的亲戚张厉生是国民党中枢要员,都不敢出面过问,保安司令部「最后审判」时,同意两位山东籍的立法委员听审观察,两立委不敢出席。人人都怕那个「自下而上」的办案方式,军法当局可 以运用这个方式「祸延」任何跟他作对的人。独有一位老先生裴鸣宇,他是山东籍国大代表,曾经是山东省参议会的议长,他老人家始终奔走陈情,提出二十六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,指出判决书十四项错误,虽然案子还是这样判定了,还是执行了,还是多亏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献,使天下后世知道冤案之所以为冤,也给最 后迟来的平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裴老是山东的好父老,孙中山先生的好信徒。
本案「平反」,已是四十七年以后,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、葛雨琴接过正义火炬,更难得民进党立委谢聪敏慷慨参与,谢委员以致力为二二八受害人争公道受人景仰,胸襟广阔,推己及人。在这几位立委以前,也曾有侠肝义胆多次努力,得到的答复是「为国家留些颜面」!这句话表示他们承认当年暗无天日,仍然没有勇气面对光明,只为国家留颜面,不为国家留心肝。所谓国家颜面成了无情的面具,如果用这块面具做挡箭牌,一任其伤痕累累,正好应了什麽人说的一句话:爱国 是政治无赖汉最后的堡垒。
选文试读:(二)与特务共舞
一九七0年十一月,台北司法调查局逮捕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,十一天后,沉之岳局长约我见面。他很客气,我第一次正式见到第一层级的特务首长,二十年来,我一直处于细胞和外围份子的困扰之中,这一下子算是熬出了头!
这好像是一个很坏的开始,看起来我像是李荆荪案的关係人。他们注意我很久很久了,为甚麽让我在这样的时刻有这样一步发展呢,我忍不住要来个假设,我有「假设癖」,这些假设都无法求証,「无解」就是大幸。
消息灵通的人士说,李副总「进去」以后,调查人员提出一些人的名字,要他一一作出分析,某人的性格怎样,思想怎样,交游和言行怎样。荆公认为国民党只用奴才,不用人才,以致许多人「压在阴山背后」。谁才是人才呢,我在中广受荆公赏识,调查人员大概没有漏掉我的名字,荆公偏爱,大概把我称赞了一番,当时沉局长创造调查局的现代史,吸纳人才,大破大立,他也许想测验我的「底气」。
他问我对调查局现在的工作有甚麽意见,调查局以后应该怎样做,这是何等事,岂容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一个文人妄议?我不敢回答。大约一个月之后,他的新闻联络室主任请我吃饭,一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陪同,馆子裡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,隔断杂音。联络官又把那两个问题提出来,我依然惶恐逊让。
我以为事情可以搪塞过去了。
又过了一些时候,广播圈裡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串门子,带来一瓶洋酒,我只好请他吃饭,时间地点都约好了。当天上午,他打电话来说,有两位朋友也想参加,希望我同意,我只有欢迎。进了舘子,才知道一共五个客人,都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份子,他们抢先付了帐,提出建议,以后每一个月或两个月聚会一次,轮流作东,这一次算他们发起,下一次轮到我,我只有答应。
他们在一家观光饭店裡找到一个甚麽厅,面积宽大,中午生意冷清,只有我们一桌,客人上菜以后,连服务生也不见了。他们非常客气,点菜一定要我点头,我说话的时候,大家一致静听。下一次约会定在甚麽时候?如果我说没有时间参加,他们延期,即使一延再延,也耐心等候。这个聚会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国为止,他们都是中生代精英,有才能有背景,前程远大,那一个都比我强,怎麽会这样迁就?这叫做「不寻常的事」。
果然不寻常,有一天谈到我新买的房子,我说那一排公寓前院后院都没有围牆,住户想把前后的空地围起来,工程师说,依照建筑法规这样行不通,但是你们可以「违章」,管区警员负责举报违章,你们得先使他「没看见」。于是里长挨家收集红包,去找警员商量,大家惟恐碰钉子,里长回来报告「他收下了」,人人笑逐颜开,一排围牆立刻兴工完成。我说五十年代大家都穷,提起贪污咬牙切齿,现在七十年代老百姓有钱,行贿是一种乐趣,官员收贿是顺应民意。我说现在有人主张台湾要有反对党,其实反对党早就有了,「特种酒家」发挥反对党的功能,你在那裡满足官员的酒色之慾,可以改变许多事情。……那晓得几个星期以后,里长挨家拜访,他说管区警员神色慌张,上面来调查围牆的事了,住户要统一口径才好。…….
蒋经国有一篇文章,题目是<风雨中的宁静>,他描述山间一条瀑布奔腾而下,瀑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洞窟,一对知更鸟在裡面做窝,几隻小鸟也孵出来了,瀑布看似凶脸,其实好像布帘一样保障了他们的安全,蒋经国如此比喻国际变局下的台湾。我说这个知更鸟的意象太小太柔了,那有中兴气象,我说想当年北伐完成,国民党中央颁布青年十二守则,党国元老戴传贤执笔写成「前言」,那是何等气势!说到这裡,我顺口「秀」了一下我受的党国教育,我立即把守则前言背诵出来:
总理立承先啓后救国救民之大志,创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宏规,领导国民革命,兴中华,建民国。于今全国同胞皆能一德一心共承遗教者,斯乃我总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,亦即中国列祖列宗天下为公大道大德之所感。今革命基础大立,革命主义大行,………
你看这段话裡有多少「大」,真是大气磅礡,大义凛然,大智大勇,大破大立,你看那时候的国民党多有志气,多有信心,当年的大鹏现在怎麽变成了知更鸟!没过多久,蒋经国提出施政的大原则,他要「开大门,走大路,当大任,成大事」。
我一看,这是怎麽了,莫非他们改变了做法,停止「引蛇出洞」,开始吹箫引凤,言者无罪,集大下之智为己智,可能吗?我已骑虎难下,每次聚会,五架「窃听器」当面打开,我必须表示坦诚。我想了又想,多年来一隻笔在手,总希望那一篇那一段那一句能影响当道,帮他们多积一粒沙那麽小的德,提醒他们,少造一粒沙那麽大的业,因果微妙,难测寸心,怎知得失!现在有这麽一个明显有效的管道,我很难抗拒它的诱惑。
我决心继续探险。我说高雄附近有个地方叫「覆金鼎」,金鼎象徵江山政权,上面怎可加上一个「覆」字?不久,蒋经国南巡,他和当地父老闲话风土,轻描淡写提了一句,覆金鼎可以改成「金鼎」。
我说红包象徵吉祥,送红包收红包都习以为常,如果政府向习俗挑战,最好在官文书中给红包改个名字,让它象徵罪恶或耻辱。于是蒋经国跟记者们闲谈的时候说,红包要改称「臭包」。
谈到买房子,我说银行的房屋贷款限八年分期还清,这种规定向人民大众传递甚麽样的讯息?政府对将来有没有信心,难道台湾只有八年安定繁荣?如果八年以后中共佔领台湾,你留着那些钱干甚麽?给中共接收?我说房屋贷款的期限应该放宽为二十年三十年,向欧美看齐,政府更要在国计民生方面强调长程计画,外商投资来盖大楼,合作计画说五十年以后怎样,七十年以后怎样,媒体报导要从这些地方着眼,大楼开工、施工、竣工、启用,大众要从电视新闻看见这些画面。我出国前,这两件事都实现了,我出国后,新闻局推出一句口号:「明天会更好」。
我一面跟这些朋友例行餐叙,同时我跟调查局的关係也继续发展,沈局长对我说,外界一向觉得调查局很神祕,其实调查局是堂堂正正的司法机关,除了工作机密,没有不可告人之处,他已经把设在新店的调查局本部变成青年学生旅行参观的一站,他也想使用传播媒体为调查局做些宣传,这是新闻联络室的业务,希望我从旁襄助。
后来那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送些文件给我看,大概是调查局的简介和过去发佈的新闻稿之类,我说这样写已经很好,局长还想怎样改变呢?联络官说局长希望这些文件能提高文学水准,我说局本部发佈的文稿不能太「文学」,文字修辞容易造成误解,我说文学应该是作家作出来的第二手传播,「二手传播」一词于焉产生。
后来联络官说,局长想拍一部纪录片,对外报导调查员训练成长的过程,由训练的内容延申,显示调查局的任务和工作方法,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,看了这部纪录片以后,可以知道调查局完全现代化了,这是一条光明大道,沉局长希望我能担任「编剧」。他们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,看过新闻局拍製的纪录片,其中有我参与。
纪录片由这位年轻的联络官担任导演,他文质彬彬,敏捷而含蓄,有学士学位,可说是新型调查员的代表,新闻界对他很有好感。为了编写脚本,我和他多次见面,得到许多指教。拍片期间,沈局长三次召我谈话,先是指示剧本的重点,第二次他提出一个问题,这部片子要不要有他的镜头?他想知道我这个外人的看法。第三次是陪他看毛片,这次经验很特殊。
地点在某处的製片厰,凡是製片厰,大概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,那条街我从未到过,我坐调查局派来的车子前往,车到街口我们下车步行,两旁都是台式楼房,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调查员凭窗下看,手裡拿着无线电话,好像向下一站通报我们的行踪。然后我们登上一栋二楼,房子很破。裡面有灯有座,像小型剧场。接待人员指定我坐在第二排第二个座位,等了一会。灯光熄灭,一个黑影走进来,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子上,他是沈局长,这时另一个黑影突然坐在我的身旁,也就是沈局长的后面,他是一位调查员,然后是放映影片。
片子拍得很好,一流的专业水准,时间超过一个半小时,似乎太长。节奏也稍欠灵活。后来导演向我解释,这是因为各部门都要有些镜头辑入,无法照剪接的要求取捨。我知道我还有机会对着画面修改旁白,没有用心细看。放映完毕,灯光未亮,沉局长起身离去,坐在我身旁的调查员紧随其后。局长下楼以后,全场恢復照明,谁也没说一句话,我坐原车回家,一路上想:「伺候沈局长可真不容易啊」!
这部纪录片的用处很多,在调查员训练班,这是一页教材,在局本、这是款待参观人士的一个项目,在各地调查站,这是一件文宣,片头字幕有我的名字,我一度惹人另眼相看,处处沾光,不过我离开台湾的日子近了。
那时美国推行「双语教育」,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文,学校得先用他的母语教他,这样中国孩子就需要中文教材和师资。新泽西州「西东大学」承联邦政府委托,成立「双语教程发展中心」,远东研究院院长杨觉勇博士主持,他到台北物色一名中文编辑,小说家、画家王蓝介绍了我。王蓝字果之,此时已尊为「果老」。
那时流行的说法,「人生有三恨」:一恨抗战八年没到过重庆,二恨胜利復员没到过北京,三恨反共抗俄没到过美国,我已三恨有其二,很想有一点弥补,我动了心。
人生果然如戏剧,许多线索平行发展而又相互缠绕。沈局长约集新闻工作者茶话,我也去了,他邀人不少,大半是採访主任这一层次的从业员,会场也没有甚麽形式。局长闲话家常,谈笑风生,显示他的风趣和平易,他用「漫谈」的方式而自有重点,他强调(现在)调查局问案绝对没有「刑求」(用刑逼供),科学办案,一切讲証据,根本用不着刑求。他也一再说,有人认为调查局是个「黑店」,进来以后再也休想走出去,这些人大错特错,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可以自由辞职,有些新进调查员还得到辅导转业。
各报都根据沈局长的谈话发佈了消息。我并不是採访新闻的记者,他也要我亲耳听见,必有用意。又过了几个月,新闻连络室主任打电话来,调查局这一届新进调查员的训练快结业了,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参加他们的结业旅行。
他已经问我过三次了。我久闻沈局长彷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风格改造调查局,新进调查员一律是大学毕业的青年,仪表足以与外交官和空军飞行官相比,必须品行端正,教养良好,志趣高尚,训练中发现瑕疵随时淘汰,训练的课程聘请第一流学者担任,这个样子的调查局是蒋经国时代的新风景,新希望,有缘一见也是眼福,他第一次问我的时候,我没有考虑,随口答应。
他第二次再问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,这一趟结业旅行为甚麽邀我参加?这些新锐将来难免担任祕密任务,我何必去看见他们?结业旅行由局长率领,第一级主管全部参加,我一路上要受多少拘束?这些念头一一闪过,只因为已经答应了邀请,难以反悔,还是说了一声「好」。
第三次再问,我的想法就複杂了,这样一件事为甚麽要问我三次?他们岂是健忘之人?我想起修女出家,教会给她一段时间慎重考虑,前后三次问她是否改变主意,三诺之后,百年定矣,再想退出,就是叛教。我正在做出国的大梦,那时出境条件严苛,手续繁複,一根线都能把你当蚂蚱拴住,我好容易从中广退休,好容易把幼狮文化公司的职位还给痖弦,老牛过窗櫺,全仗一身乾淨,倘若再结尘缘,又是飞絮沾泥,我立刻婉转辞谢了。
申请出国的人要经过安全调查,我得找个机会说出我对特务机构的看法,争取他们的了解,这时,我们那个特殊的餐会对我非常重要。我一再拿特务当做话题,在我们那个餐桌上,这个话题太敏感了,同席的人显然没料到我敢碰,我已决心孤注一掷,神色泰然,笼中鸟要唱歌,听歌的人也许在笼子上加一把锁,也许打开笼门让我飞,我的话似褒似眨,由他们领受,得马失马,靠我的运气。
我陆陆续续说了许多话,总而言之,特务好比外科医生,手中有刀,手术台上没有细菌,没人喜欢外科医生,但是每一家医院都必须设置外科。有一个年轻人问他的父亲,你当初为甚麽要做外科医生,手有鲜血,面无表情,眼科有多好,端庄斯文,轻巧细腻,心脏科有多好,结识一大群董事长总经理,增加对社会的影响力,我不知那位父亲是怎样回答的,我想最好的答案是、人类需要外科医生,而且需要最好的外科医生。
我不客气的说,当年特务素质很低,社会的观感是、一个人甚麽都不能做才去做特务,这些人好比文革时期的赤脚医生,医疗失误罄竹难书,但是也勉强维持了公众的健康。
我不客气的说,他们多少人受过日本特务的苦刑拷打,几番死去活来,多少人被中共特务追捕,三九寒天,山林荒野中昼伏夜出,留下终身痼疾,多少人中共枪杀了他的父亲,把他的妻子儿女发配到边疆开荒,这是甚麽样的遭遇,这样的遭遇如何影响了他的人格和性情!五十年代,台湾靠这一批人支撑危局,他们如果发疯了,那可怎麽办,皇天在上,后土在下,总算列祖列宗英灵未泯,总算中华文化种子未死,总算坚百忍以图成的「领袖」身教言教,他们办案时有些行为令人髮指,可是总体来看,他们还算有节制,目的和手段之间还能分出本末体用,他们的罪恶本来可以更多。
三十年后浪前浪,我说今天在台湾做特务,他必须是第一流人才,他们干那一行都会出色,但是他们选择了第一志愿。我顺口举例把自己分析了一下,像我这样一块料,做人作文都比人家慢一拍,斗智毫无胜算,我的生理构造有「麻烦症候群」,体能很差,斗力是输家,别说是去当特务了,如果特务拿我做对象,也害他们浪费光阴,我实在不能为恶,不足为害,何况我已超过五十岁,常常觉得不耐烦,这表示我已停止成长,失去可塑性,今生一切都要到此为止了。
这样谈下去,无可避免有一天谈到党外的街头运动。我忍不住说,游行示威是群众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,他们那裡是造反?那裡就动摇了国本?土地是老百姓的,他们要站在上面叫一叫、跳一跳,何必一定把他们赶回家中关上门窗?当然,有些地方群众可以去,有些地方群众不能去,游行示威之前,照例有个组织发动的阶段,警备总部照例老早掌握了情况,这时可以透过中间人谈条件,游行示威由你,规矩范围由我,彼此约法三章,先小人后君子,那些民间领袖都有事业前途,参加示威的人都在安居乐业,他们并非亡命的暴民,几个人能赴汤蹈火?
我忍不住说,从一九四六年起,我就看见「咱们国民党」犯一个错误,拿群众当敌人,双方断绝一切管道,静等着拉弓放箭。军队只受过作战训练,没受过镇暴训练,以作战的方式镇暴,反应过当,破坏太大。现在政府要立刻派人到美国考察学习,把他们镇暴的观念方法和装备搬来,重新训练治安部队,赶上时代。(后来新闻报导说,政府派人到美国考察去了。)
这样谈下去,有一天我忍不住讲了一个故事,我说有一个人患了重病,送进医院,经过长期疗养,精神渐渐恢復,他对医生对护士的不满也天天增加,终于有一天,他躺在病床上,看见医生进门,抓起药瓶向医生投去,医生急忙躲闪,药瓶在门上撞碎了。护士大惊而医生大喜,他说这一掷力道不小,可见病人的体力恢復,也可见我的治疗完全奏效。
国民党人总是说,两位蒋总统治理台湾,尽心尽力,他们在大陆上从没对任何一省的人这样好,即使是浙江省,因此党人认为台湾人应该听话,这种想法太陈旧了。人性複杂幽深,因果关係岂是如此简单,何况现在已非「崇功报德」的时代,公认人民大众有权利喜新厌旧,反復无常,政治家为而不有,随时可以被遗忘,被曲解,被替代,他要从政就得「牺牲享受,享受牺牲」,悲天悯人,为苍生作奉献,老天爷给他的报偿,只是汉明威笔下那一付鱼骨头,也就是一页青史。
如果用专政暴力捍卫政权呢,咳,我说那倒是一个办法,可惜我们都老了,没有力气提起步枪冲上去,咳,我们的儿女也都不听话,政治信念不能遗传。我说「服食求长生,多为药所误」,南韩李起鹏辣手铁腕,咱们望尘莫及,最后王朝倾复,李起鹏命令一家五口在客厅集合,他亲自开枪杀死妻子儿女,然后自杀,咳,我狠狠的说了一句:「咱们也没那个种」!
回想起来,我当时也失去了控制,但是他们爱听,显然还有更多的期待,长日漫漫,独立、联俄、两岸谈判、一一见肺见肝。我每次赴约都像教授上课或者像被告出庭,你得准备一些「说法」填塞时间,我不能缺席,不能沉默,因为我心中有贪有痴,我的出国手续已办到最后一步,等待出境许可,如果拿不到出境証,前功尽弃,拿到了出境証,那才是画龙点睛,我如果託任何人关说疏通,那就是「着相」,我从未把这个话题提上餐桌,他们也没任何人问我,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心上压着这麽一块石头,看我怎样搬开。我相信每次餐会以后,他们写回去的报告一定影响最后的判决,我只能顺着他们的需求诚实「招供」,讨好他们的上司,为我出境涂抹滑润剂。
他们几次把话题引到蒋经国传位的问题,看样子我若想走开,对这个话题就没法避开。我那时还能喝几杯陈年绍兴,黄汤下肚,舌片微麻,好,那就担当最大的风险,吐出「酒后真言」。那时盛传「蒋经国培植蒋孝武继位接班」,我断言蒋家第三代不宜再执政了,因为人民会厌倦,从头算起,祖父在位三十二年,父亲将要在位十二年,父子相承可能四十五年,孙辈是难以为继了!
蒋介石总统连任五次,人民大众已经流露了幽默感,民间笑谈,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蒋中正,第二任总统于右任(我又来担任),第三任总统吴三连(吾第三次连任),第四任总统赵丽莲(照例连任),第五任总统任百年(做总统一直做到死)。我说民间称中山先生为国父,称蒋公为「国兄」,称蒋经国为「国姪」,称蒋孝武为「国孙」,讽嘲之情溢于言表,第三代接班?大众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
我把蒋经国的才干度量谋略统驭大大称颂一番,我说当初那些跟他争位的人,吴国桢,陈诚,孙立人,周至柔,谁也都要差他一截。我甚至说,他有些地方比他的老太爷更杰出,他一样可以完成北伐抗战那样的大业,只是没有那样的机会罢了。那时数当代人物,没人敢说蒋介石位居第二,但是如果说他的儿子比他更好,我想是安全的,人人知道蒋经国很想走出他父亲的盛名笼罩,自创新局,他提出「大有为」的口号,台湾的篆刻家每人刻了一方印章献给他,印文全是「大有为」,联合开了一次展览。(这些印章现在不知落到郁裡去了)
我说诗人书法家于还素写过一副对联:「一身是胆终非虎,万里无云欲化龙。」大家认为写出蒋经国的局限,上一句说他主观条件不足,下一句说他客观环境不利,但是我说,经国先生现在还有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,足以使他绕过蒋介石这座大山,站进历史舞臺的强区,他可以解严,恢復平时状态,建立民主制度。
民主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词,国民党将因此失去政权。执政党要尽力延长执政的时间,那是理所当然,但是我说,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维持政权,一旦行到水穷处,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云起时,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权。我说专制并不能使你永远握有政权,想想中国历代王朝「失国」,都与民主无关,结局如何悲惨!得国不易,失国更难,我特别一个字一个字的说: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,就是解决如何「失国」。
我发表了我受党化教育的独门心得,我说依照中山先生的设计,国民党最后要还政于民,这是三民主义的中国特色,如果抽去这个核心价值,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就和苏共中共很难区分。有人说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是假的,在警备司令看来它可以是假的,在中山先生它应该是真的,蒋公一直在这条路上走,他死在半路上,谁能断言他是假?我说历史发展到这一步,全看经国先生怎麽做,如果他建立民主体制,让人民投票选择政府,大家都是真的,中山先生的理想终于实现,蒋公的人格浑然完整,经国先生的历史地位也巍然确立。
一九五○年,中共宣佈全面「解放」中国大陆,我在台北听到一则口传的掌故。当年国民党联俄容共,进行北伐,消灭了军阀割据,国民党内部有一群人主张吸收马列主义,遵从苏联领导,推行共产制度,倘若那样,国民党就是中国共产党,「马列史毛」会写成「马列史蒋」,那样就不会有国共内战,国民党一直稳坐江山,也不致于偏安台湾了。怪只怪党国元老戴传贤,他痛哭流涕向蒋公进谏,请蒋公一定要到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」这边排队,这才受到时代潮流的淘汰。这种思想也随着国民党人来到台湾,有人主张亡羊补牢,知过必改,毛泽东怎样统治大陆,咱们也照样统治台湾。……我说你想想这是多麽可怕的声音,如果真的这样办了,今后国民党留给「台湾人」的是多麽残酷的一架机器,在那架机器操作之下,咱们一小撮「外省人」怎麽活,你如果留下的是民主制度,这四百万人是一个很大的「压力团体」,它有运作的空间,咱们子子孙孙都可以在台湾立足。……..
我说了一个小时,没人反问,没人打岔,没人咳嗽,没人动筷子,大厅内静如广播电臺的发音室,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朋友,右手插进西装裡抚摩左胸,好像心血管有点小毛病,我想他是操作衣袋裡的袖珍录音机。我说完了,他们也没有任何评论,没有一句回应,任我如此这般放肆一番,好像与他们毫不相干。我究竟闯了大祸还是立了大功,一时茫然。
时间近了,我也辞穷了,我对他们说,我本是内战的残魂剩魄,来到国民党的残山剩水,吃资本家的残茶剩饭,三十年来看遍多少人为党国牺牲,也看遍多少人使党国为他牺牲,党国左手来右手去,以不足奉有馀,我们是各有因缘莫羡人,纵然下台一条虫,我也是益虫,不做害虫,我们依然支持国民党,只有在国民党治下我才有做一条益虫的可能。(我这算是澈底交心了,你们饶了我吧!)
也许有关係,也许没关係,我领到出境証。
我在出入境管理处门口遇见一个熟人,他问我来做甚麽,我举起手中那张纸:「我来领贞节牌坊」。一时又是喜悦,又是辛酸,好像很充实,又像很空虚,台湾混了三十年,患得患失为了这张纸,也太没出息了。
回到家,我拿起电话,几乎想告诉果老,把西东大学的聘函退了,可是我还是打给旅行社买了机票。
时维一九七八年九月,起飞那天清早,定期聚餐的那五个朋友中间的一位请我吃早点,松山飞机场旁边开了一家观光级的豆浆店,精致雅洁。我们在那裡坐定,他举起茶杯对我说:「我代表本单位给你送行,你可以出国。」好像出境証还不算数似的。他们从来无人表露另一种身份,突如其来我吃了一惊,立刻想起三国演义「闻雷失筯」,我说「怎麽冒出来一个本单位,你吓了我一跳!」
我想起来治安当局花样多,我认识聋盲学校的一位教师,她曾把我的<开放的人生>译成点字当做教材,她出国的故事那才叫精采,人已经坐在飞机裡,又被广播器叫下来,没收了出境証和护照,治安人员欲擒故纵,只是要观察她拿到出境証以后的一言一行。
飞机平稳滑行,忽然窗框歪斜,圆山大饭店缩小成模型,机身转弯,我看见隐隐山峰水气淋漓,有如米芾的画。我觉得肚脐好痛,像是拉断了脐带,然后就是云天万里。「你可以出国」,那位朋友没骗我,感谢同桌共餐的五位朋友,我想他们帮了忙,我更钦佩沈之岳局长,他老成谋国,大开大阖。
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湾宝岛,七月,澎湖即发生「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」冤案,那是对我的当头棒喝,也是对所有的外省人一个下马威。当 年中共席捲大陆,人心浮动,蒋介石自称「我无死所」,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,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, 一件「二二八」事件慑伏了本省人,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伏了外省人,就这个意义来说,两案可以相提并论。
烟台联中冤案尤其使山东人痛苦,历经五○年代、六○年代进入七○年代,山东人一律「失语」,和本省人之于「二二八」相同。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「八 千子弟」中的一个分子,我们也从不忍拿这段历史做谈话的材料。有一位山东籍的小说家对我说过,他几次想把冤案经过写成小说,只是念及「身家性命」无法落 笔,「每一次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无耻。」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。
编剧家赵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学生,他去世后,编剧家张文祥写文章悼念,谈到当年在澎湖被迫入伍,常有同学半夜失踪,「早晨起床时只见鞋子」,那 些都是强迫入伍后不甘心认命的学生,班长半夜把他装进麻袋丢进大海。这是我最早读到的记述。小说家张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,他的中篇小说〈海兮〉以山东流 亡学生在澎湖的遭遇为背景,奔放沉痛,「除了人名地名」以外,直言不讳。然后我读到周绍贤〈澎湖冤案始末〉、傅维宁〈一桩待雪的冤案〉、李春序 〈傅文沉冤待雪读后〉,直到〈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〉、张敏之夫人回忆录〈十字架上的校长〉,连人名地名都齐备了。
可怜往事从头说:内战后期,国军节节败退,山东流亡学生一万多人奔到广州,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出面交涉,把这些青年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。 当时约定,让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,十七岁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,天下有事投入战场,天下无事升班升学。当时,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澎湖当家作主的陈诚都批准这样安排。
一九四九年六月,学生分两批运往澎湖, 登轮者近八千人, 后来号称八千子弟。七月十三日,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,把年满十六岁的学生,连同年龄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「标准」的学生,一律编入步兵团。学生举手呼 喊「要读书不要当兵」,士兵上前举起刺刀刺伤了两个学生,司令台前一片鲜血,另有士兵开枪射击,几个学生当场中弹。三十年后,我读到当年一位流亡学生的追述,他说枪声响起时,广场中几千学生对着国旗跪下来。这位作者使用「汴桥」做笔名,使我想起「汴水流,泗水流……恨到归时方始休」,可怜的孩子,他们捨死忘生追赶这面国旗,国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块布。
编兵一幕,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监督进行。流亡学校的总校长张敏之当面抗争,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动学生造反。李振清虽然是个大老粗,到底行军打仗升到将军,总学会了几手兵不厌诈,他居然对学生说:「你们都是我花钱买来当兵的!一个兵三块银元!」他这句话本来想分化学生和校长的关係,殊不知把 张敏之校长逼上十字架,当时学生六神无主,容易轻信谣言,这就是群众的弱点,英雄的悲哀,自来操纵群众玩弄群众的人才可以得到现实利益!为他们真诚服务却要忧谗畏讥。张敏之是个烈士,「烈士殉名」,他为了证明人格清白,粉身碎骨都不顾,只有与李振清公开决裂,决裂到底。
张敏之身陷澎湖,托人带信给台北的秦德纯,揭发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。咳,张校长虽然与中共斗争多年,竟不知道如何隐藏夹带一封密函,带信使者在澎湖码头上船的时候,卫兵从他口袋裡搜出信来,没收了。张敏之又派烟台联合中学的另一位校长邹鑑到台北求救,邹校长虽然也有与中共斗争的经验,沿途竟没有和「假想敌」捉迷藏,车到台中就被捕了。
最后,张敏之以他惊人的毅力,促使山东省政府派大员视察流亡学生安置的情形,教育厅长徐轶千是个好样的,他会同教育部人士来到澎湖。李振清矢口否认强迫未成年的学生入伍,徐厅长请李振清集合编入军伍的学生见面,李无法拒绝,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带到海边拾贝壳。徐轶千告诉参加大集合的学生, 「凡是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学生站出来,回到学校去读书!」队伍中虽然还有幼年兵,谁也不敢出头乱动。张敏之动了感情,他问学生: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读书吗? 现在为什麽不站出来?徐厅长在这裡,教育部的长官也在这裡,你们怕什麽?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,你们错过了这个机会,再也没有下一次了!行列中有十几个孩子 受到鼓励,这才冒险出列。李振清的谎言拆穿了。后来办案人员对张敏之罗织罪名,把这件事说成煽动学生意图製造暴乱,张校长有一把摺扇,他在扇上亲笔题字, 写的是「穷则独搧其身,达则兼搧天下」,这两句题词也成了「煽动」的证据。
徐轶千对张敏之说:「救出来一个算一个,事已至此,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!」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,于是着手「做案」,这个「做」字是肃谍专家的内部术语,他们常说某一个案子「做」得漂亮,某一个案子没有「做」好。做案如做文章,先要立意,那就是烟臺联中有一个庞大的匪谍组织,鼓动山东流亡学生破坏建军。立意之后蒐集材料,蒐集材料由下层着手,下层人员容易屈服。那时候办「匪谍」大案都是自下而上,一层一层株连。
做案如作文,有了材料便要布局。
办案人员逮捕了一百多个学生(有数字说涉案师生共一百零五人)疲劳审问,从中选出可用的讯息,使这些讯息发酵、变质、走味,成为罪行。办案人员锁定 其中五个学生,按照各人的才能、仪表、性格,强迫他们分担罪名,那作文成绩优良的,负责为中共作文字宣传;那强壮率直的,参与中共指挥的暴动;那文弱的, 觉悟悔改自动招供。于是这五个学生都成了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分团长。
每一个分团当然都有团员,五个分团长自己思量谁可以做他的团员,如果实在想不出来,办案人员手中有「情报资料」,可以提供名单,证据呢,那时办「匪 谍」,只要有人在办案人员写好的供词上盖下指纹,就是铁证如山。这麽大的一个组织,单凭五个中学生当然玩不转,他们必然有领导,于是张敏之成了中共胶东区执行委员,邹鑑成了中共烟台区市党部委员兼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主任。
办案人员何以能够心想事成呢?唯一的法术是酷刑,所以审判「匪谍」一定要用军事法庭祕密进行。澎湖军方办案人员花了四十天功夫,使用九种酷刑,像神创造天地一样,他说要有什麽就有了什麽。最后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,判定两位校长(张敏之、邹鑑)五名学生(刘永祥、张世能、谭茂基、明同乐、王光耀) 共同意图以非法方式颠复政府,各处死刑及褫夺公权终身。这一年, 张敏之四十三岁,邹鑑三十八岁。同案还有六十多名学生,押回澎湖以「新生队」名义管训,这些学生每人拿着一张油印的誓词照本宣读,声明脱离他从未加入过的 中共组织,宣誓仪式拍成新闻片,全省各大戏院放映,一生在矮簷下低头。当时保安司令是陈诚,副司令是彭孟缉。
那时候,军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,五千多名入伍的学生从此与世隔绝。还有两千四百多名学生(女生和十六岁以下的孩子),李振清总算为他们成立了一所子弟学校,继续施教,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。下一步,教育部在台中员林成立实验中学,使这些学生离开澎湖。
我是后知后觉,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凑出整个案情。我也曾是流亡学生,高堂老母寿终时不知我流落何处,我常常思念澎湖这一群流亡学生的生死祸福,如 同亲身感受。有一天我忽然触类旁通,「烟台联中匪谍案」不是司法产品,它是艺术产品,所有的材料都是「真」的,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却是「假」的,因为 「假」,所以能达到邪恶的目的,因为「真」,所以「读者」坠入其中不觉得假。狱成三年之后,江苏籍的国大代表谈明华先生有机会面见蒋介石总统,他义薄云天,代替他所了解、所佩服的张敏之申冤,蒋派张公度调查,张公度调阅案卷,结论是一切合法,没有破绽!酷刑之下,人人甘愿配合办事人员的构想,给自己捏造 一个身分,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分,有了身分自然有行为,各人再捏造行为,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,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,这个结构有在内在的逻辑,互补互依,自给自足。
今天谈论当年的「白色恐怖」应该分成两个层次:有人真的触犯了当时的禁令和法律,虽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当的,当时执法者和他们的上司还可以採取「纯法律观点」原谅自己,另外一个层次,像张敏之和邹鑑,他们并未触法(即使是恶法!),他们是教育家,为国家教育保护下一代,他们是国民党党员,尽力实现党的理想,那些国民政府的大员、国民党的权要,居然把这样的人杀了!虽有家属的申诉状,山东大老裴鸣宇的辨冤书,监察委员崔唯吾的保证书,一概置之不顾,他对自己的良心和子孙如何交代?我一直不能理解。难道他们是把这样的案子当做艺术品来欣赏?艺术欣赏的态度是不求甚解,别有会心,批准死刑犹如在节目单上圈选一个戏码,完全没有「绕室徬徨掷笔三歎」的必要。
他们当时杀人毫不迟疑,真相大白时又坚决拒绝为受害人平反。说到平反,冤案发生时,山东省主席秦德纯贵为国防部次长,邹鑑的亲戚张厉生是国民党中枢要员,都不敢出面过问,保安司令部「最后审判」时,同意两位山东籍的立法委员听审观察,两立委不敢出席。人人都怕那个「自下而上」的办案方式,军法当局可 以运用这个方式「祸延」任何跟他作对的人。独有一位老先生裴鸣宇,他是山东籍国大代表,曾经是山东省参议会的议长,他老人家始终奔走陈情,提出二十六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,指出判决书十四项错误,虽然案子还是这样判定了,还是执行了,还是多亏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献,使天下后世知道冤案之所以为冤,也给最 后迟来的平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裴老是山东的好父老,孙中山先生的好信徒。
本案「平反」,已是四十七年以后,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、葛雨琴接过正义火炬,更难得民进党立委谢聪敏慷慨参与,谢委员以致力为二二八受害人争公道受人景仰,胸襟广阔,推己及人。在这几位立委以前,也曾有侠肝义胆多次努力,得到的答复是「为国家留些颜面」!这句话表示他们承认当年暗无天日,仍然没有勇气面对光明,只为国家留颜面,不为国家留心肝。所谓国家颜面成了无情的面具,如果用这块面具做挡箭牌,一任其伤痕累累,正好应了什麽人说的一句话:爱国 是政治无赖汉最后的堡垒。
选文试读:(二)与特务共舞
一九七0年十一月,台北司法调查局逮捕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,十一天后,沉之岳局长约我见面。他很客气,我第一次正式见到第一层级的特务首长,二十年来,我一直处于细胞和外围份子的困扰之中,这一下子算是熬出了头!
这好像是一个很坏的开始,看起来我像是李荆荪案的关係人。他们注意我很久很久了,为甚麽让我在这样的时刻有这样一步发展呢,我忍不住要来个假设,我有「假设癖」,这些假设都无法求証,「无解」就是大幸。
消息灵通的人士说,李副总「进去」以后,调查人员提出一些人的名字,要他一一作出分析,某人的性格怎样,思想怎样,交游和言行怎样。荆公认为国民党只用奴才,不用人才,以致许多人「压在阴山背后」。谁才是人才呢,我在中广受荆公赏识,调查人员大概没有漏掉我的名字,荆公偏爱,大概把我称赞了一番,当时沉局长创造调查局的现代史,吸纳人才,大破大立,他也许想测验我的「底气」。
他问我对调查局现在的工作有甚麽意见,调查局以后应该怎样做,这是何等事,岂容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一个文人妄议?我不敢回答。大约一个月之后,他的新闻联络室主任请我吃饭,一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陪同,馆子裡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,隔断杂音。联络官又把那两个问题提出来,我依然惶恐逊让。
我以为事情可以搪塞过去了。
又过了一些时候,广播圈裡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串门子,带来一瓶洋酒,我只好请他吃饭,时间地点都约好了。当天上午,他打电话来说,有两位朋友也想参加,希望我同意,我只有欢迎。进了舘子,才知道一共五个客人,都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份子,他们抢先付了帐,提出建议,以后每一个月或两个月聚会一次,轮流作东,这一次算他们发起,下一次轮到我,我只有答应。
他们在一家观光饭店裡找到一个甚麽厅,面积宽大,中午生意冷清,只有我们一桌,客人上菜以后,连服务生也不见了。他们非常客气,点菜一定要我点头,我说话的时候,大家一致静听。下一次约会定在甚麽时候?如果我说没有时间参加,他们延期,即使一延再延,也耐心等候。这个聚会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国为止,他们都是中生代精英,有才能有背景,前程远大,那一个都比我强,怎麽会这样迁就?这叫做「不寻常的事」。
果然不寻常,有一天谈到我新买的房子,我说那一排公寓前院后院都没有围牆,住户想把前后的空地围起来,工程师说,依照建筑法规这样行不通,但是你们可以「违章」,管区警员负责举报违章,你们得先使他「没看见」。于是里长挨家收集红包,去找警员商量,大家惟恐碰钉子,里长回来报告「他收下了」,人人笑逐颜开,一排围牆立刻兴工完成。我说五十年代大家都穷,提起贪污咬牙切齿,现在七十年代老百姓有钱,行贿是一种乐趣,官员收贿是顺应民意。我说现在有人主张台湾要有反对党,其实反对党早就有了,「特种酒家」发挥反对党的功能,你在那裡满足官员的酒色之慾,可以改变许多事情。……那晓得几个星期以后,里长挨家拜访,他说管区警员神色慌张,上面来调查围牆的事了,住户要统一口径才好。…….
蒋经国有一篇文章,题目是<风雨中的宁静>,他描述山间一条瀑布奔腾而下,瀑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洞窟,一对知更鸟在裡面做窝,几隻小鸟也孵出来了,瀑布看似凶脸,其实好像布帘一样保障了他们的安全,蒋经国如此比喻国际变局下的台湾。我说这个知更鸟的意象太小太柔了,那有中兴气象,我说想当年北伐完成,国民党中央颁布青年十二守则,党国元老戴传贤执笔写成「前言」,那是何等气势!说到这裡,我顺口「秀」了一下我受的党国教育,我立即把守则前言背诵出来:
总理立承先啓后救国救民之大志,创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宏规,领导国民革命,兴中华,建民国。于今全国同胞皆能一德一心共承遗教者,斯乃我总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,亦即中国列祖列宗天下为公大道大德之所感。今革命基础大立,革命主义大行,………
你看这段话裡有多少「大」,真是大气磅礡,大义凛然,大智大勇,大破大立,你看那时候的国民党多有志气,多有信心,当年的大鹏现在怎麽变成了知更鸟!没过多久,蒋经国提出施政的大原则,他要「开大门,走大路,当大任,成大事」。
我一看,这是怎麽了,莫非他们改变了做法,停止「引蛇出洞」,开始吹箫引凤,言者无罪,集大下之智为己智,可能吗?我已骑虎难下,每次聚会,五架「窃听器」当面打开,我必须表示坦诚。我想了又想,多年来一隻笔在手,总希望那一篇那一段那一句能影响当道,帮他们多积一粒沙那麽小的德,提醒他们,少造一粒沙那麽大的业,因果微妙,难测寸心,怎知得失!现在有这麽一个明显有效的管道,我很难抗拒它的诱惑。
我决心继续探险。我说高雄附近有个地方叫「覆金鼎」,金鼎象徵江山政权,上面怎可加上一个「覆」字?不久,蒋经国南巡,他和当地父老闲话风土,轻描淡写提了一句,覆金鼎可以改成「金鼎」。
我说红包象徵吉祥,送红包收红包都习以为常,如果政府向习俗挑战,最好在官文书中给红包改个名字,让它象徵罪恶或耻辱。于是蒋经国跟记者们闲谈的时候说,红包要改称「臭包」。
谈到买房子,我说银行的房屋贷款限八年分期还清,这种规定向人民大众传递甚麽样的讯息?政府对将来有没有信心,难道台湾只有八年安定繁荣?如果八年以后中共佔领台湾,你留着那些钱干甚麽?给中共接收?我说房屋贷款的期限应该放宽为二十年三十年,向欧美看齐,政府更要在国计民生方面强调长程计画,外商投资来盖大楼,合作计画说五十年以后怎样,七十年以后怎样,媒体报导要从这些地方着眼,大楼开工、施工、竣工、启用,大众要从电视新闻看见这些画面。我出国前,这两件事都实现了,我出国后,新闻局推出一句口号:「明天会更好」。
我一面跟这些朋友例行餐叙,同时我跟调查局的关係也继续发展,沈局长对我说,外界一向觉得调查局很神祕,其实调查局是堂堂正正的司法机关,除了工作机密,没有不可告人之处,他已经把设在新店的调查局本部变成青年学生旅行参观的一站,他也想使用传播媒体为调查局做些宣传,这是新闻联络室的业务,希望我从旁襄助。
后来那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送些文件给我看,大概是调查局的简介和过去发佈的新闻稿之类,我说这样写已经很好,局长还想怎样改变呢?联络官说局长希望这些文件能提高文学水准,我说局本部发佈的文稿不能太「文学」,文字修辞容易造成误解,我说文学应该是作家作出来的第二手传播,「二手传播」一词于焉产生。
后来联络官说,局长想拍一部纪录片,对外报导调查员训练成长的过程,由训练的内容延申,显示调查局的任务和工作方法,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,看了这部纪录片以后,可以知道调查局完全现代化了,这是一条光明大道,沉局长希望我能担任「编剧」。他们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,看过新闻局拍製的纪录片,其中有我参与。
纪录片由这位年轻的联络官担任导演,他文质彬彬,敏捷而含蓄,有学士学位,可说是新型调查员的代表,新闻界对他很有好感。为了编写脚本,我和他多次见面,得到许多指教。拍片期间,沈局长三次召我谈话,先是指示剧本的重点,第二次他提出一个问题,这部片子要不要有他的镜头?他想知道我这个外人的看法。第三次是陪他看毛片,这次经验很特殊。
地点在某处的製片厰,凡是製片厰,大概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,那条街我从未到过,我坐调查局派来的车子前往,车到街口我们下车步行,两旁都是台式楼房,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调查员凭窗下看,手裡拿着无线电话,好像向下一站通报我们的行踪。然后我们登上一栋二楼,房子很破。裡面有灯有座,像小型剧场。接待人员指定我坐在第二排第二个座位,等了一会。灯光熄灭,一个黑影走进来,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子上,他是沈局长,这时另一个黑影突然坐在我的身旁,也就是沈局长的后面,他是一位调查员,然后是放映影片。
片子拍得很好,一流的专业水准,时间超过一个半小时,似乎太长。节奏也稍欠灵活。后来导演向我解释,这是因为各部门都要有些镜头辑入,无法照剪接的要求取捨。我知道我还有机会对着画面修改旁白,没有用心细看。放映完毕,灯光未亮,沉局长起身离去,坐在我身旁的调查员紧随其后。局长下楼以后,全场恢復照明,谁也没说一句话,我坐原车回家,一路上想:「伺候沈局长可真不容易啊」!
这部纪录片的用处很多,在调查员训练班,这是一页教材,在局本、这是款待参观人士的一个项目,在各地调查站,这是一件文宣,片头字幕有我的名字,我一度惹人另眼相看,处处沾光,不过我离开台湾的日子近了。
那时美国推行「双语教育」,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文,学校得先用他的母语教他,这样中国孩子就需要中文教材和师资。新泽西州「西东大学」承联邦政府委托,成立「双语教程发展中心」,远东研究院院长杨觉勇博士主持,他到台北物色一名中文编辑,小说家、画家王蓝介绍了我。王蓝字果之,此时已尊为「果老」。
那时流行的说法,「人生有三恨」:一恨抗战八年没到过重庆,二恨胜利復员没到过北京,三恨反共抗俄没到过美国,我已三恨有其二,很想有一点弥补,我动了心。
人生果然如戏剧,许多线索平行发展而又相互缠绕。沈局长约集新闻工作者茶话,我也去了,他邀人不少,大半是採访主任这一层次的从业员,会场也没有甚麽形式。局长闲话家常,谈笑风生,显示他的风趣和平易,他用「漫谈」的方式而自有重点,他强调(现在)调查局问案绝对没有「刑求」(用刑逼供),科学办案,一切讲証据,根本用不着刑求。他也一再说,有人认为调查局是个「黑店」,进来以后再也休想走出去,这些人大错特错,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可以自由辞职,有些新进调查员还得到辅导转业。
各报都根据沈局长的谈话发佈了消息。我并不是採访新闻的记者,他也要我亲耳听见,必有用意。又过了几个月,新闻连络室主任打电话来,调查局这一届新进调查员的训练快结业了,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参加他们的结业旅行。
他已经问我过三次了。我久闻沈局长彷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风格改造调查局,新进调查员一律是大学毕业的青年,仪表足以与外交官和空军飞行官相比,必须品行端正,教养良好,志趣高尚,训练中发现瑕疵随时淘汰,训练的课程聘请第一流学者担任,这个样子的调查局是蒋经国时代的新风景,新希望,有缘一见也是眼福,他第一次问我的时候,我没有考虑,随口答应。
他第二次再问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,这一趟结业旅行为甚麽邀我参加?这些新锐将来难免担任祕密任务,我何必去看见他们?结业旅行由局长率领,第一级主管全部参加,我一路上要受多少拘束?这些念头一一闪过,只因为已经答应了邀请,难以反悔,还是说了一声「好」。
第三次再问,我的想法就複杂了,这样一件事为甚麽要问我三次?他们岂是健忘之人?我想起修女出家,教会给她一段时间慎重考虑,前后三次问她是否改变主意,三诺之后,百年定矣,再想退出,就是叛教。我正在做出国的大梦,那时出境条件严苛,手续繁複,一根线都能把你当蚂蚱拴住,我好容易从中广退休,好容易把幼狮文化公司的职位还给痖弦,老牛过窗櫺,全仗一身乾淨,倘若再结尘缘,又是飞絮沾泥,我立刻婉转辞谢了。
申请出国的人要经过安全调查,我得找个机会说出我对特务机构的看法,争取他们的了解,这时,我们那个特殊的餐会对我非常重要。我一再拿特务当做话题,在我们那个餐桌上,这个话题太敏感了,同席的人显然没料到我敢碰,我已决心孤注一掷,神色泰然,笼中鸟要唱歌,听歌的人也许在笼子上加一把锁,也许打开笼门让我飞,我的话似褒似眨,由他们领受,得马失马,靠我的运气。
我陆陆续续说了许多话,总而言之,特务好比外科医生,手中有刀,手术台上没有细菌,没人喜欢外科医生,但是每一家医院都必须设置外科。有一个年轻人问他的父亲,你当初为甚麽要做外科医生,手有鲜血,面无表情,眼科有多好,端庄斯文,轻巧细腻,心脏科有多好,结识一大群董事长总经理,增加对社会的影响力,我不知那位父亲是怎样回答的,我想最好的答案是、人类需要外科医生,而且需要最好的外科医生。
我不客气的说,当年特务素质很低,社会的观感是、一个人甚麽都不能做才去做特务,这些人好比文革时期的赤脚医生,医疗失误罄竹难书,但是也勉强维持了公众的健康。
我不客气的说,他们多少人受过日本特务的苦刑拷打,几番死去活来,多少人被中共特务追捕,三九寒天,山林荒野中昼伏夜出,留下终身痼疾,多少人中共枪杀了他的父亲,把他的妻子儿女发配到边疆开荒,这是甚麽样的遭遇,这样的遭遇如何影响了他的人格和性情!五十年代,台湾靠这一批人支撑危局,他们如果发疯了,那可怎麽办,皇天在上,后土在下,总算列祖列宗英灵未泯,总算中华文化种子未死,总算坚百忍以图成的「领袖」身教言教,他们办案时有些行为令人髮指,可是总体来看,他们还算有节制,目的和手段之间还能分出本末体用,他们的罪恶本来可以更多。
三十年后浪前浪,我说今天在台湾做特务,他必须是第一流人才,他们干那一行都会出色,但是他们选择了第一志愿。我顺口举例把自己分析了一下,像我这样一块料,做人作文都比人家慢一拍,斗智毫无胜算,我的生理构造有「麻烦症候群」,体能很差,斗力是输家,别说是去当特务了,如果特务拿我做对象,也害他们浪费光阴,我实在不能为恶,不足为害,何况我已超过五十岁,常常觉得不耐烦,这表示我已停止成长,失去可塑性,今生一切都要到此为止了。
这样谈下去,无可避免有一天谈到党外的街头运动。我忍不住说,游行示威是群众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,他们那裡是造反?那裡就动摇了国本?土地是老百姓的,他们要站在上面叫一叫、跳一跳,何必一定把他们赶回家中关上门窗?当然,有些地方群众可以去,有些地方群众不能去,游行示威之前,照例有个组织发动的阶段,警备总部照例老早掌握了情况,这时可以透过中间人谈条件,游行示威由你,规矩范围由我,彼此约法三章,先小人后君子,那些民间领袖都有事业前途,参加示威的人都在安居乐业,他们并非亡命的暴民,几个人能赴汤蹈火?
我忍不住说,从一九四六年起,我就看见「咱们国民党」犯一个错误,拿群众当敌人,双方断绝一切管道,静等着拉弓放箭。军队只受过作战训练,没受过镇暴训练,以作战的方式镇暴,反应过当,破坏太大。现在政府要立刻派人到美国考察学习,把他们镇暴的观念方法和装备搬来,重新训练治安部队,赶上时代。(后来新闻报导说,政府派人到美国考察去了。)
这样谈下去,有一天我忍不住讲了一个故事,我说有一个人患了重病,送进医院,经过长期疗养,精神渐渐恢復,他对医生对护士的不满也天天增加,终于有一天,他躺在病床上,看见医生进门,抓起药瓶向医生投去,医生急忙躲闪,药瓶在门上撞碎了。护士大惊而医生大喜,他说这一掷力道不小,可见病人的体力恢復,也可见我的治疗完全奏效。
国民党人总是说,两位蒋总统治理台湾,尽心尽力,他们在大陆上从没对任何一省的人这样好,即使是浙江省,因此党人认为台湾人应该听话,这种想法太陈旧了。人性複杂幽深,因果关係岂是如此简单,何况现在已非「崇功报德」的时代,公认人民大众有权利喜新厌旧,反復无常,政治家为而不有,随时可以被遗忘,被曲解,被替代,他要从政就得「牺牲享受,享受牺牲」,悲天悯人,为苍生作奉献,老天爷给他的报偿,只是汉明威笔下那一付鱼骨头,也就是一页青史。
如果用专政暴力捍卫政权呢,咳,我说那倒是一个办法,可惜我们都老了,没有力气提起步枪冲上去,咳,我们的儿女也都不听话,政治信念不能遗传。我说「服食求长生,多为药所误」,南韩李起鹏辣手铁腕,咱们望尘莫及,最后王朝倾复,李起鹏命令一家五口在客厅集合,他亲自开枪杀死妻子儿女,然后自杀,咳,我狠狠的说了一句:「咱们也没那个种」!
回想起来,我当时也失去了控制,但是他们爱听,显然还有更多的期待,长日漫漫,独立、联俄、两岸谈判、一一见肺见肝。我每次赴约都像教授上课或者像被告出庭,你得准备一些「说法」填塞时间,我不能缺席,不能沉默,因为我心中有贪有痴,我的出国手续已办到最后一步,等待出境许可,如果拿不到出境証,前功尽弃,拿到了出境証,那才是画龙点睛,我如果託任何人关说疏通,那就是「着相」,我从未把这个话题提上餐桌,他们也没任何人问我,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心上压着这麽一块石头,看我怎样搬开。我相信每次餐会以后,他们写回去的报告一定影响最后的判决,我只能顺着他们的需求诚实「招供」,讨好他们的上司,为我出境涂抹滑润剂。
他们几次把话题引到蒋经国传位的问题,看样子我若想走开,对这个话题就没法避开。我那时还能喝几杯陈年绍兴,黄汤下肚,舌片微麻,好,那就担当最大的风险,吐出「酒后真言」。那时盛传「蒋经国培植蒋孝武继位接班」,我断言蒋家第三代不宜再执政了,因为人民会厌倦,从头算起,祖父在位三十二年,父亲将要在位十二年,父子相承可能四十五年,孙辈是难以为继了!
蒋介石总统连任五次,人民大众已经流露了幽默感,民间笑谈,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蒋中正,第二任总统于右任(我又来担任),第三任总统吴三连(吾第三次连任),第四任总统赵丽莲(照例连任),第五任总统任百年(做总统一直做到死)。我说民间称中山先生为国父,称蒋公为「国兄」,称蒋经国为「国姪」,称蒋孝武为「国孙」,讽嘲之情溢于言表,第三代接班?大众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
我把蒋经国的才干度量谋略统驭大大称颂一番,我说当初那些跟他争位的人,吴国桢,陈诚,孙立人,周至柔,谁也都要差他一截。我甚至说,他有些地方比他的老太爷更杰出,他一样可以完成北伐抗战那样的大业,只是没有那样的机会罢了。那时数当代人物,没人敢说蒋介石位居第二,但是如果说他的儿子比他更好,我想是安全的,人人知道蒋经国很想走出他父亲的盛名笼罩,自创新局,他提出「大有为」的口号,台湾的篆刻家每人刻了一方印章献给他,印文全是「大有为」,联合开了一次展览。(这些印章现在不知落到郁裡去了)
我说诗人书法家于还素写过一副对联:「一身是胆终非虎,万里无云欲化龙。」大家认为写出蒋经国的局限,上一句说他主观条件不足,下一句说他客观环境不利,但是我说,经国先生现在还有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,足以使他绕过蒋介石这座大山,站进历史舞臺的强区,他可以解严,恢復平时状态,建立民主制度。
民主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词,国民党将因此失去政权。执政党要尽力延长执政的时间,那是理所当然,但是我说,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维持政权,一旦行到水穷处,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云起时,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权。我说专制并不能使你永远握有政权,想想中国历代王朝「失国」,都与民主无关,结局如何悲惨!得国不易,失国更难,我特别一个字一个字的说: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,就是解决如何「失国」。
我发表了我受党化教育的独门心得,我说依照中山先生的设计,国民党最后要还政于民,这是三民主义的中国特色,如果抽去这个核心价值,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就和苏共中共很难区分。有人说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是假的,在警备司令看来它可以是假的,在中山先生它应该是真的,蒋公一直在这条路上走,他死在半路上,谁能断言他是假?我说历史发展到这一步,全看经国先生怎麽做,如果他建立民主体制,让人民投票选择政府,大家都是真的,中山先生的理想终于实现,蒋公的人格浑然完整,经国先生的历史地位也巍然确立。
一九五○年,中共宣佈全面「解放」中国大陆,我在台北听到一则口传的掌故。当年国民党联俄容共,进行北伐,消灭了军阀割据,国民党内部有一群人主张吸收马列主义,遵从苏联领导,推行共产制度,倘若那样,国民党就是中国共产党,「马列史毛」会写成「马列史蒋」,那样就不会有国共内战,国民党一直稳坐江山,也不致于偏安台湾了。怪只怪党国元老戴传贤,他痛哭流涕向蒋公进谏,请蒋公一定要到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」这边排队,这才受到时代潮流的淘汰。这种思想也随着国民党人来到台湾,有人主张亡羊补牢,知过必改,毛泽东怎样统治大陆,咱们也照样统治台湾。……我说你想想这是多麽可怕的声音,如果真的这样办了,今后国民党留给「台湾人」的是多麽残酷的一架机器,在那架机器操作之下,咱们一小撮「外省人」怎麽活,你如果留下的是民主制度,这四百万人是一个很大的「压力团体」,它有运作的空间,咱们子子孙孙都可以在台湾立足。……..
我说了一个小时,没人反问,没人打岔,没人咳嗽,没人动筷子,大厅内静如广播电臺的发音室,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朋友,右手插进西装裡抚摩左胸,好像心血管有点小毛病,我想他是操作衣袋裡的袖珍录音机。我说完了,他们也没有任何评论,没有一句回应,任我如此这般放肆一番,好像与他们毫不相干。我究竟闯了大祸还是立了大功,一时茫然。
时间近了,我也辞穷了,我对他们说,我本是内战的残魂剩魄,来到国民党的残山剩水,吃资本家的残茶剩饭,三十年来看遍多少人为党国牺牲,也看遍多少人使党国为他牺牲,党国左手来右手去,以不足奉有馀,我们是各有因缘莫羡人,纵然下台一条虫,我也是益虫,不做害虫,我们依然支持国民党,只有在国民党治下我才有做一条益虫的可能。(我这算是澈底交心了,你们饶了我吧!)
也许有关係,也许没关係,我领到出境証。
我在出入境管理处门口遇见一个熟人,他问我来做甚麽,我举起手中那张纸:「我来领贞节牌坊」。一时又是喜悦,又是辛酸,好像很充实,又像很空虚,台湾混了三十年,患得患失为了这张纸,也太没出息了。
回到家,我拿起电话,几乎想告诉果老,把西东大学的聘函退了,可是我还是打给旅行社买了机票。
时维一九七八年九月,起飞那天清早,定期聚餐的那五个朋友中间的一位请我吃早点,松山飞机场旁边开了一家观光级的豆浆店,精致雅洁。我们在那裡坐定,他举起茶杯对我说:「我代表本单位给你送行,你可以出国。」好像出境証还不算数似的。他们从来无人表露另一种身份,突如其来我吃了一惊,立刻想起三国演义「闻雷失筯」,我说「怎麽冒出来一个本单位,你吓了我一跳!」
我想起来治安当局花样多,我认识聋盲学校的一位教师,她曾把我的<开放的人生>译成点字当做教材,她出国的故事那才叫精采,人已经坐在飞机裡,又被广播器叫下来,没收了出境証和护照,治安人员欲擒故纵,只是要观察她拿到出境証以后的一言一行。
飞机平稳滑行,忽然窗框歪斜,圆山大饭店缩小成模型,机身转弯,我看见隐隐山峰水气淋漓,有如米芾的画。我觉得肚脐好痛,像是拉断了脐带,然后就是云天万里。「你可以出国」,那位朋友没骗我,感谢同桌共餐的五位朋友,我想他们帮了忙,我更钦佩沈之岳局长,他老成谋国,大开大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