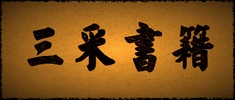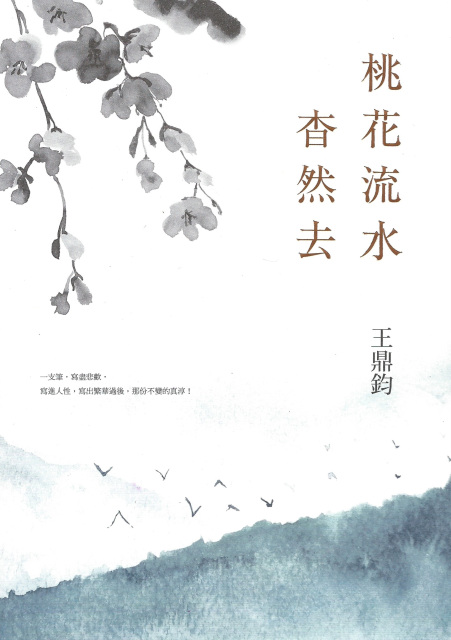桃花流水沓然去 (繁體字版)
SKU:
$0.00
Unavailable
per item
出版發行: 台北馬可孛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年: 2018 (2018年 10月初版)
總頁數: 384
ISBN 978-957-875-935-0
內容簡介(王鼎鈞的雜文集):
王鼎鈞寫了三十多年的雜文專欄,由青壯寫到老年。起初,雜文的特色是「短小精悍,尖銳犀利,以攻擊的姿勢指向假想敵,文壇的前輩說它是匕首,是標槍。」這就和文學的散文不同。王鼎鈞說,他並不喜歡寫這樣的文章。
王鼎鈞說,後來社會轉型,雜文專欄也改變風格,「悻悻」不見了,「彬彬」來 眼前,血性減少,情趣增加,殺氣減少,逸氣增加,武斷減少,商量增加。以談天代駡陣,以天女散花代金剛怒目,以輕裘緩帶代披甲戴盔,以與人為善代嫉 惡如仇,不是對敵人喊話,是和朋友對話,不是把墨水變成別人的血,是把自己的血變成墨水。他稱這種改變是雜文解甲歸田,雜文向散文歸化。
這本<桃花流水杳然去>,收錄了王鼎鈞「向散文歸化」了的雜文,風評極佳。
出版年: 2018 (2018年 10月初版)
總頁數: 384
ISBN 978-957-875-935-0
內容簡介(王鼎鈞的雜文集):
王鼎鈞寫了三十多年的雜文專欄,由青壯寫到老年。起初,雜文的特色是「短小精悍,尖銳犀利,以攻擊的姿勢指向假想敵,文壇的前輩說它是匕首,是標槍。」這就和文學的散文不同。王鼎鈞說,他並不喜歡寫這樣的文章。
王鼎鈞說,後來社會轉型,雜文專欄也改變風格,「悻悻」不見了,「彬彬」來 眼前,血性減少,情趣增加,殺氣減少,逸氣增加,武斷減少,商量增加。以談天代駡陣,以天女散花代金剛怒目,以輕裘緩帶代披甲戴盔,以與人為善代嫉 惡如仇,不是對敵人喊話,是和朋友對話,不是把墨水變成別人的血,是把自己的血變成墨水。他稱這種改變是雜文解甲歸田,雜文向散文歸化。
這本<桃花流水杳然去>,收錄了王鼎鈞「向散文歸化」了的雜文,風評極佳。
Sold Out
選文試讀:(一)由子宮到天堂
「在亞當的時代,天堂是家;在我們的時代,家是天堂。」
人的第一個「家」是母腹,宗教家說人的前世經驗可以帶到今生,教育家說人在母腹裡的經驗支配長大後的行為,人在這個「大後方」接受最初的裝備。
人在母腹裡的姿勢最舒適,環境最安全,全身被打擊的面積最小,重要的器官都保護起來。痛苦時我們採取的姿勢,睡眠時我們採取的姿勢,羅丹雕刻的「沉思者」也近乎這個姿勢。
人類的第一個「家」是女性建立的。
然後我們需要第二個家,於是有父母的愛和勇氣包圍在我們四周,他們的胸脯最溫暖,臂膀裡最安全。家是母腹放大,家是天堂的派出所,所以說「上帝不能親自照顧每一個人,所以創造了母親。」或者可以加添幾個字,他也創造了父親,父母各自代表上帝的這一面和另一面。
照小篆的寫法,「家」字屋頂下面還有牆,像舞臺拆去「第四面牆」那樣,露出裡面的「豕」,於是巴金借小說人物之口說,「家」是屋頂下面一窩豬!這句話很鋒利,成為名言,影響極大,基督教會頗受壓力,只得為「天家」另造一字,寶蓋下面一個「佳」字。巴金鼓吹革命,煽動青年走出家庭,參加無產階級大家庭,大破大立,六親不認。學者認為「豕」字代表家畜,代表居有定所,代表由畜牧進入農業。女子飼養家畜,代表這時有了婚姻制度。這第二個家也靠女性建立。
今天戶籍上的「家」指結婚生子,否則只算「共同生活戶」,一門出入。我們說家家戶戶,兩者大同而小異。這個生兒養女的家也是女性建立起來,嬰兒的哭聲是沙漠駝鈴,丟在客廳地毯上的玩具是人類的新石器時代,兒女是自己的回顧,青春期、反抗期、都有你已喪失的優點,也重複你犯過的錯誤。兒女是祖先再生,高祖子孫盡龍準,祖父曾祖父的腔調身段都可複製,賈母是老祖宗,寶玉是「小祖宗」,如此這般也許可以解釋中國人人為何偏愛親生。
房屋公司的銷售標語說:「家是人生最大的投資」,標語旁邊畫著一棟房子。這句話和巴金相反,但同樣出自廣告天才之手。「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,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,」有人說中國人喜歡造牆,真的嗎,怎麼歐洲也有城堡,印第安人也有 wall st. ,美國也用小洋房代表「美國夢」。阿姆斯壯在月球上說「回家真好」。他們不是愛牆,他們愛那子宮的樣式。
最後,我們會有第四個家,宇宙,蛋白包著蛋黃,子宮的樣式,天家。「必有童女,懷孕生子」,道成肉身,完成人的救贖,這第四個家也是女性建立的。
依宗教家的說法,我們都是旅行的人,人生如寄,古人有「寄寄園」,庭園暫時寄放在我的名下,「我」又暫時被寄放在世上。終有一天乘風歸去,瓊樓玉宇,別是一番溫暖。
「回家真好」,回到第四個家更好,我們的家又是天堂,亞當失去的、我們又得到了。人必須四個家都有,這一代中國人的悲劇是國太多、家太少。天國,天堂,天家,國太嚴重,堂太空洞,最好是天家。
餘波蕩漾…….
蘇北坡:「在亞當的時代,天堂是家;在我們的時代,家是天堂。」好句子!何以沒註明是誰說的?
十二姨:很多格言都失掉出處,「失敗是成功之母」是誰說的?
楊揚洋洋:水果摘下來,忘了是那棵樹,也不想知道種樹的人,這是人性忘恩的証明。
寧為女人:甚麼年代了?還把女人定位在生兒養女?
十二姨:這篇文章的主題是「家」,用小品體裁,總不能把花木蘭、居里夫人、南丁格爾、德蕾莎修女都寫進去吧?
蘇北坡:我也來咬文嚼字,「寧為女人」,這個「寧」字透露了多少不得已不甘心,哈哈!得罪了!
江上風:我讀這篇文章,想起「君子之道,造端乎夫婦,及其至也,察乎天地。」寫得好!
十二姨:不要被意識型態遮蓋了文學趣味。
選文試讀:(二)「南京大屠殺」三段論
「南京大屠殺」,靜聽百家爭鳴,想到這個重大的慘案至今有了三個面目。
第一,抗戰文宣中的大屠殺。文宣的手段是訴諸愛國心和敵愾心,目的在激起報仇雪恨的義憤,情緒掛帥,立場至上。要知道那時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到處任意殺害無辜,人人親眼所見親耳所聞,跟全部人命總數相比,南京一地其小焉者也,經驗主義壓倒証據主義,數字究竟多少並不重要,宣傳效果百分之百成功。
第二,戰爭結束以後,出現了歷史記述中的大屠殺。史家講究史學方法,歷史著述須符合專業標準,它的手段和目的另有不同,以致衍化出「南京大屠殺」和「南京屠殺」兩個觀念。某些日本人以此為借口,堅持沒有南京大屠殺,請注意那個「大」字,至於「屠殺」,一般日本人的心目中還是存在的。
南京大屠殺究竟有多「大」?答案是三十四萬人。南京屠殺又究竟有多「小」?據說根據現有的資料,大約三萬多人。這九倍的差距怎麼辦?咱們政府戰後沒有認真調查,而今去日苦多,已是一籌莫展。抗戰八年,國民政府連自己的士兵戰死了多少都沒有準確的數字,何況老百姓!更何况敵人佔領區的老百姓?
國民政府以南京大屠殺概括戰爭時期敵軍的全面殺戮,又以局部証據概括南京的全部殺戮,多年反復爭辯造成一種印象,好像日軍只在南京一地殺人,而所殺的人數並不很多,這真是弄巧成拙!怎麼辦呢,有心人想到拍電影,這似乎是一個補救的辦法,電影是藝術,藝術可以「局部代全體」,藝術能使人感同身受、不求甚解,歷史沉睡電影醒,也許死結賴巧手而解。
電影拍出來了,可惜觀眾很少,新聞報導說,有些電影院臨時輟演,因為沒有人買票。如此這般產生第三個問題,電影裡的南京大屠殺該是甚麼樣子?電影講求電影語言,電影美學,藝術境界,恐怕還得有迴腸蕩氣的故事,視聽之娛的穿插,僅僅標榜真材實料,那是歷史觀念,反復宣示「凡是愛國的中國人都應該去看」,那是文宣觀念,電影藝術既有異於文宣也有別於歷史。
一九九年年底,美國<時代周刊>登出一篇文章,列舉二十世紀的各項特徵,其中一項竟是大屠殺流行!我想到當年有一種思潮,為了推動世界進步,一部份人(精英)有權消滅另一部份人(劣等份子),因此可以理直氣壯殘殺異己,何止一個日本軍閥放手蠻幹!時至今日,受害族群之中好像只有猶太人作出了成功的回應?
我們多少人好像還沈醉在抗戰文宣的效果之中,使酒駡座,向電影觀眾要愛國心,多少人明知債主已銷毀了貸款的憑証,卻主張欠債的人自動歸還,向日本政府要道德。多少人要求下一代爭氣、成器、將來以強制弱,討回公道,向子孫要補償。可有人討論:對這個不加引號的南京大屠殺,我們如何向全人類的後代作有效的轉述?如果我們僅有抗戰文宣的思維,斷簡殘編的史料,血淋淋的紀錄片?
補足歷史記述有待發現新的史料,要等奇蹟。化全民記憶為藝術,創造經典之作,風靡當代,留傳久遠,要靠天才。我不祈求「河出圖、洛出書」,只希望發現<安妮日記>、<揚州十日記>。我不尋找救世主、真龍天子,只希望知道誰是斯蒂芬·斯皮爾伯格(辛德勒名單導演)。歷史不容你不信,電影不由你不看,如此這般大屠殺才會成為鎔鑄國魂的原料,才有向世界控訴的喉舌。
選文試讀:(三)記者與作家
七七抗戰發生以前,中國的青年人有朝氣,肯上進。那時有個說法,青年最認同的形象是:黃埔軍校學生,新聞記者,土木工程師,外科醫生。(那時一般人認為中醫長於內科拙於外科,亟須西醫補救,合格的西醫為稀有傑出的人才。)
那時的新聞記者大概穿深色的中山裝,胸前左上的口袋裡插著「金星牌」自來水鋼筆,傳說他的那枝筆有魔力,他寫下誰的名字誰頭疼發燒。那時 的工程師穿工人的粗布服裝,大手大腳,時常從口袋裡掏出計算尺來東量西量,據說他的這把尺能量出來地球多大。外科醫生給人的強烈印象是戴口罩和橡皮手套, 那時沒有塑膠,大家說他殺人不用償命,因為沒留指紋。那時黃埔軍校的學生還鄉探親,只見他穿黃呢軍服,戴白手套,天子門生,鐵打的少尉,紮武裝帶,佩短 劍,他用那把劍殺人不償命,因為他殺的是敵人。
新聞記者布衣傲王侯,見官大一級。新聞記者總是飯局不斷,「和尚吃十方,記者吃十一方,和尚也要招待記者」。有一老兵說,抗戰 八年,道路流離,他看見多少人挨餓,新聞記者總有人供應三餐,所以他後來把女兒嫁給記者。內戰時期,長春斷糧,官方說餓死十二萬人,野史說餓死三十萬人, 有錢的人拿一棟房子換一碗米,房子還有、米沒有了。除了達官,有三種人不會餓死,軍人,美女,新聞記者。
文藝沙龍找我來談說新聞記者和作家的因緣,我看兩者難分難解,有人做作家做不好去做記者,也有人做記者做得很好去做作家,失敗的作家有兩條路,做記者或做教員,成功的記者也有兩條路,做官或者做作家。報紙是記者的前方,作家的後方,文壇是記者的後方,作家的前方。大英百科全書有一個很長的名單介紹「作家記者」或「記者作家」,用詞顛倒中寓有褒貶,前者文學成就大於新聞建樹,後者似乎相反。
有些好記者也是好作家,在我心目中外國有海明威,馬克吐溫,蕭伯納,毛姆,約翰根室,莫拉維亞;中國有蕭軍,徐訏,蕭乾,張恨水,王藍,范長江,曹聚仁,南宮搏。還有梁啟超和于右任似乎可以入列,但是又未便高攀。
現在南京大學有「作家記者班」,廣東有「作家記者俱樂部」,網站有記者作家網,山東大學有文學新聞傳播學院,這些都顯示作家記者合流。新聞寫作的方式是否因此發生改變?記者越來越像作家、還是作家越來越像記者?這是新聞研究所的論文題目。
新聞記者不是容易做成的,他得有外向的肉體,內向的靈魂,他熱情勇敢,同時冷靜周密,兩個不同的靈魂裝在一個腔子裡。他是好人,懂得一切做壞事的方法,他不做壞事做好事,但是他為了做成一件好事往往要先做壞事,相反的特質,矛盾統一,稀有難得,上帝用特殊的材料造成的破格完人。
新聞記者天天遇挑戰,時時有壓力,他吃的是英雄飯,憑一身武藝,水裡來火裡去。他是一個「不能輸的人」,而勝利的果實很快就腐爛了,運動員拿到金牌,他的榮譽可以維持四年,報紙記者的勝利只有二十四小時,電視記者只有兩小時,廣播記者也許只有十分鐘。同行競爭,你死我活,聚光燈照在誰身上,誰立時成為箭垛,相識滿天下,忽然最孤獨,春天迎接挑戰,路上沒有蝴蝶,夏天迎接挑戰,樹上沒有葉子。
我在報社打工的時候社會新聞掛帥,在很大的程度上,社會新聞就是犯罪新聞,採訪社會新聞的記者是王牌、是紅人。我跟一位社會版的明星記者 鄰桌而坐,只見他每天挺胸抬頭出去,垂頭喪氣回來,他忽然發現人民的道德水準極高!天下太平無事,找不到兇殺、貪污、強姦、拐帶人口、捲款潛逃。一天沒有 獨家,他在採訪組貶值,一星期沒有頭條,他在老闆眼中貶值,一個月還不見驚世駭俗,他在同行中失去尊嚴。有一天這位明星記者喟然歎曰:「我去殺一個人,回來自己寫,他們誰也寫不過我。」記者身處此境,父子不能相救,兄弟不能相顧,夫妻同床異夢,同行都是冤家。他們羨慕作家,一同說故事,一同朗誦新作,切磋 琢磨,種種佳話美談。
一般而論,作家的工作很安全, 新聞記者卻上了「最危險的職業」排行榜,名次緊緊排在警察礦工之後,位居第三。(服兵役是權利義務,並非職業,所以軍人沒計算在內。)我喜歡恩尼派爾,他的風格至今留在我的作品裡,他在硫磺島戰役採訪時被日軍的狙擊手射死。二戰戰場留下的紀錄,有一次「十天內死了七名記者」,有一次「一顆砲彈炸死五名記者」。據保護記者協會發表的訊息,二○○三年全球有六十二名記者殉職,其中十五名死於伊拉克,單是四月八日這一天之內就有七名記者受傷,次年五月二十八日,伊拉克境內又有日本記者兩人死亡,六月十日,BBC記者一死一傷。二○○三這一年,全世界有一百三十三個記者被本國政府逮捕坐牢,還有許多記者因揭發 黑幕遭黑社會打傷。
我們恭維記者,當面稱他是名記者、大記者,周勻之在他的「記者生活雜憶」中自嘲,名記者是「有名字的記者」,大記者是「年紀大的記者」。名記者不易,大記者更難,腦筋快,膽子大,運氣好,一條新聞可以名滿天下,若要大格局,大氣派,恐怕百年難遇一人。
何謂大記者?一九五三年,好萊塢拍過一部電影叫 「羅馬假期」,奧黛麗赫本演一個年輕的公主,葛雷葛萊畢克演一個美國記者,情節不必細表,公主天真爛漫,沒有防人之心,記者推動事件發展,乘機「偷拍」了她許多照片,足可寫一篇轟動兩國的新聞,那樣記者可以得大名,公主的聲譽和王室的尊嚴卻要受到嚴重傷害。最後記者把照片送給公主做訪美紀念,他放棄了新聞報導,等於放棄了普立茲獎。人散劇終,葛雷葛萊畢克獨立大廳之內,導演用仰角給他拍了一個鏡頭,拔高他的形象。這時他是「大記者」,不是名記者。
何謂名記者?這裡有一個真實的故事。某年非洲某一地區大旱,赤地千里,某記者驅車經過災區,烈日當空,不見人煙,只有一個幼童坐在乾裂的 土地上,奄奄一息,旁邊站著一隻兀鷹,這隻以腐肉為食的猛禽顯然在等那孩子死亡,然後啄食。記者停車拍照,然後趕回辦公地點發稿,那張照片登在各國的報紙上,我也在中文報紙上看見了,孩子又黑又瘦,衣不蔽體,脖子已無力支持頭顱,兀鷹的體積幾乎比孩子還大,目光陰沉盯住孩子的身體,背景則是一望無垠寸草不生,誰能拍 到這樣一張照片也算曠世奇緣,那位記者的大名立刻傳遍世界。有人問他那孩子後來怎樣了?他不能答覆,這就是名記者而非大記者。
名記者是新聞的產物,大記者是文化的產物。
我是讀報長大的一代,後來有聽廣播長大的一代,然後有看電視長大的一代,上網長大的一代,上帝造人,媒體加工,代代人氣質不同。看人挑擔 不吃力,作家看記者,越看越有趣,見過幾位了不起的採訪記者,上天不拘一格降人才,亦俠亦儒亦梟雄,能耐天磨真好漢,惹得詩人說到今。他們的故事今天一言難盡,不堪回首,新聞媒體慘澹經營,記者耗盡青春打前鋒,不眠不休,患得患失。世事無常,英雄無覓,回想我們當年那些貪瞋痴都隨雨打風吹去,早知道隆中高 臥,省多少六出歧山。
我不想做記者,只想做作家,人壽保險費比較便宜。記者是熊掌,作家是魚,我一直坐在魚與熊掌之間左顧右盼。作家空間較大,有不朽的作家,合時的作家,受人崇拜的作家,崇拜別人的作家。作家也不拘一格,鏗鏗鏘鏘的作家,嘻嘻哈哈的作家,奇文共賞的作家,孤芳自賞的作家,不專心的作家,不後悔的作家。有人如此介紹我:「這是最有名的作家,」對方一怔:「哦?沒聽說過!」你沒聽見過的作家仍然是作家。
選文試讀:(四)盼望宗教合作的時代來臨
唐朝的吉瑣和武則天有過一段對話:一桶水,一堆土,會發生衝突嗎?不會。水加土和成一灘泥,泥中會發生衝突嗎?也不會。若是把泥拿來做一尊佛、一尊玉皇大帝呢?那就要發生衝突。
宗教衝突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,我們不做研究,沒有學問,借著吉瑣和武則天的這一段對話來引導思考,倒也化繁為簡。世人尊崇宗教,本來是為了解決人類共同的問題,但是宗教以「具象」接引信眾,重要的宗教都有自己獨特的具象,信眾進入具象以後,宗教家要你永久停留在裡面,反而把人類分化了!這樣也許能解決一家一姓的難題,不能解決(有時反而加重了)普天普世的難題。海外有人研究為何華僑不能團結,指出「宗教信仰」為原因之一。幾乎可以說,宗教已成為割裂人群、经營壁壘、妨礙大同的最後一個因素。
2001年9月11日,紐約兩棟摩天大廈轟然崩坍,造成三千多人傷亡和經濟上的嚴重損失,也預告了宗教衝突的無窮後患。美國總統布希立刻邀請各宗教領袖聚集一堂,為和平祈禱。第二年開始,紐約市長彭博在每年最後一天舉辦早餐祈禱會,邀請各宗教領袖參加。他們似乎覺知天下事無法依賴「一神」降福,各宗教必須異中求同,始而互相包容,繼而分工合作。
我想起1975年蔣介石先生在臺北逝世,依基督教儀式營葬,主持葬禮的周聯華牧師在祈禱之前加了一句「史無前例」的話:「請全國同胞各自向你們信奉的神禱告,為總統蔣公祈福」。這句話在基督教內引起軒然大波,卻也給了我許多啟發。我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氣,我開始覺知一教一派無法包辦人類的救贖,每一家宗教都尺有所短,寸有所長。受眾有機會作其他選擇,任何一教一派無權剝奪此一權利。
我聽說原始社會部落林立,各個部落都有自己的守護神,這個「神」只保佑自己一個部落,而且幫助這一個部落去消滅別的部落,那時候,各宗教之間當然互相敵視,互相咒詛。至今仍有一些宗教,只救某一個地方的人,或只救某一個種族的人,這是「部落的宗教」,信仰這種宗教的人是很可怕的。我猜社會進化宗教也進化,各宗教同在現代社會中相處,脫胎換骨,但原始經典裡的部落色彩、狹隘的民族主義還殘留在靈魂裡,他們把經文中的部落與部落解釋為今天的本國與外國,把經文中非我族類的外邦人解釋為異教徒和沒有信仰的人,以致殺機仍在,宿仇未解,有些教派仍然以有我無敵而後快,信教的人如果能回顧歷史,就知道這種心態是世界和平人類幸福的障礙。
萬事莫如和平急,我猜宗教對抗的時代應該結束了,我們需要宗教合作的時代。各宗教的經典文本和崇拜儀式不同,经典儀式之後之上的東西可能無異,大家各以自己的說法做法去做和別人一樣的事情。以佛教和基督教為例,成佛好比是你考上了哈佛大學,應該還有很多很多大專院校讓大家受高等教育,上天堂好比你住進了曼哈頓的高等公寓,應該還有很多很多住宅讓更多的人安身.佛教基督教有共同的弘誓大願,兩路分兵進咸陽,西醫治不好的病還有中醫,火車到不了的地方還有汽車,不能坐飛机的人可以坐郵輪.人類有了佛陀又有了基督,我看是好的。
我甚至認為對佛陀的信仰可以深化對基督的信仰,對基督的信仰可以強化對
佛陀的信仰。他們的信仰沒有冲突,他們是一個信仰兩種形式,形式為內容而存在,我們順著形式求內容,我們不停留在形式上忘記內容。
當然,任何一個宗教領袖都要謀求本教的延長和擴大,他無可避免要和別的宗教競爭。依我們已有的知識,競爭要「誇張自己的優點,攻擊對方的弱點」,任何一個傳道說法的人都力稱自己的信仰唯一正確,絕對有效。中醫看病還會說「你得去看西醫」,基督教傳道人決不能說「你去試試佛教」。這是他們的苦衷,我們可以理解,但是我認為這是可以改變的,他們吸引信眾穩定信仰還可以有更好的方法,培養宗教人才的學院應該增加新的課程。
很可能最大的障礙仍在經典內容,歷史在他們之間造成很深的鴻溝,各宗教的領袖都是往昔拒絕互相見面的人物,今天能夠坐在一起吃飯祈禱,也能在低層次的技術性的事務上合作,例如救災,這是很大的進展。但是經典中惟我獨尊、排斥異類的文字猶在,目前只是存而不論,「半部論語治天下」。如果埋藏起來的種子未死,隨時可能發穿破土,我擔心他們尚未覺知,他們好比是鋼琴手,提琴手,或者鼓手,誰也不該規定世界上只准學一種樂器,他們要合起來演奏交響樂。
聖嚴法師說過一句話:宗教經典中如有妨礙世界和平的文句,現在要重新作出詮釋。他這個意見很重要,可惜沒有得到重視。如所周如,基督教在舊約時代,上帝只救以色列人,「部落的宗教」色彩濃厚,但耶穌重新作出詮釋,「世人都是上帝的兒女,」都是救贖的對象,天家的成員,基督教進入新約時代,這才成為人類的宗教。
我還記得,耶穌本來有反抗的精神,他提出好幾個煽動性的口號,例如「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、不要怕他」。他的道路很窄。後來使徒保羅重新作出詮釋,他要教會「順從掌權的,因為權柄是上帝賜予的」,天地就寬廣了。宗教靠殉道者提高,靠妥協者推廣,保羅給妥協者尋找經典支特,對基督教的發展很有助益。
我還記得,當我少小在家之時,佛教對文學創作的看法完全是負面的,世上並沒有賈寶玉其人,你居然捏造出一百萬字來,這是妄語,這是口業,死後要下拔舌地獄。我從圖畫中看見拔舌地獄的景象,兩個惡鬼像拔河,罪人的舌頭拉得很長,根深蒂固,欲斷還連,罪人痛苦的面孔和惡鬼猙獰的面孔長期對峙。據說施耐庵的子孫都是啞吧,因為他寫小說。那時候寫文章的人有罪惡感。現在「人間佛教」的說法不同了,文學家,音樂家,美術家,能創造出好作品,都是福德,人生在世欣賞好的文藝作品,也是福報。我們聽了如逢大赦,如歸故鄉,覺得佛教很有親和力。
如所周知,佛教一向認為做人和成佛兩者方向不同,修行的人要割斷塵緣,甚至脫離社會,佛門大開可是門檻甚高。等到佛教的發展在近代社會中遭到瓶頸,這才重新作出詮釋,佛法在世間,人成即佛成,修行可以和世俗行業並行不悖,甚至相輔相成,大概除了開屠宰廠。以前佛門即是空門,灰身滅志,現在佛門是大企業,許多人才找到出路,信徒湧入,佛教乃有今日一時之盛。
在很大的程度上,信徒的信仰來自宗教家對經典的詮釋,一個基督徒他信靠的並非是聖經,而是某一派神學,神學是對聖經有系統的解釋。經典不能改,詮釋可以變,佛門說「用佛法解釋外道,外道也是佛法,用外道解釋佛法,佛法也是外道」。大法官解釋法律,有時等於立法。漢傳佛教有十宗,基督教新教有兩百多個教派,都是「詮釋」造成的,詮釋能造成分歧,也能造成融合,能造成戰爭,也能造成和平。
當然此事非同小可,恐怕要佛教再出一個釋迦,基督教再出一個基督。目前可以先從內部研究著手,希望那一個基金會列為工作重點,鼓勵「學士僧」研究,鼓勵神父研究,鼓勵大學研究所讀碩士博士的人研究,辦一個專門的刊物,發表他們的論文。目前宗教領袖們只要不批駁,不歧視,「看草生長就好」。
選文試讀:(五)世界貿易中心大樓看人
今天,我到世界貿易中心去看人。這棟著名的大樓一百一十層,四一七公尺高,八十四萬平方公尺的辦公空間,可以容納五萬人辦公。樓高,薪水高,社會地位也高,生活品味也高?這裡給商家和觀光採購者留下八萬人的容積,可有誰專誠來看看那些高人?
早晨八時,我站在由地鐵站進大樓入口的地方,他們的必經之路,靜心守候。起初冷泠清清,電燈明亮,曉風殘月的滋味。時候到了,一排一排頭顱從電動升降梯裡冒上來,露出上身,露出全身,前排走上來,緊接著後排,彷彿工廠生產線上的作業,一絲不茍。
早上八點到九點,正是公共交通的尖鋒時刻。貿易中心是地鐵的大站,我守在乘客最多的R站和E站入口,車每三分鐘一班,每班車約有五百人到七百人走上來,搭乘 電梯,散入大樓各層辦公室。世貿中心共有九十五座電梯,坐電梯也有一個複雜的路線圖,一個外來的游客尋找電梯,不啻進入一座迷宮。
這些上班族個個穿黑色外衣,露出雪白的衣領,密集前進,碎步如飛,分秒必爭,無人可以遲到,也無人願意到得太早。黑壓壓,靜悄悄,走得快,腳步聲也輕。這是資本家的雄師,攻城掠地,這是資本主義的齒輪,造人造世界。是甚麼樣的模型、甚麼樣的壓力、使他們整齊劃一,不約而同?
我仔細看這些職場的佼佼者,美國夢的夢游者,頭部隱隱有朝氣形成的光圈,眼神近乎傲慢,可是又略顯驚慌,不知道是怕遲到?怕裁員?還是怕別人擠到他前面去?如果有董事長,他的頭髮應該白了,如果有總經理,他的小腹應 該鼓起來,沒有,個個正當盛年,都是配置在第一線的精兵,他們在向我詮釋白領的定義,向第三世界來者展示上流文化的表象。
我能分辨中國人、韓國人、日本人,不能分辨盎格魯撒克遜人、雅利安人、猶太人,正如他們能夠分辨俄國人、德國人,不能分辨廣東人、山東人。現在我更覺得他們的差別 極小,密閉的辦公室,常年受慘白的日光燈浸泡黃,皮膚彷彿褪色泛白,黑皮膚也好像上了一層淺淺的粙子。究竟是他們互相同化了、還是誰異化了他們?
這些人號稱在天上辦公,(高樓齊雲,辦公桌旁準備一把雨傘,下班時先打電話問地面下雨了沒有。)在地底下走路,(乘坐地鐵,穿隧而行。)在樹林裡睡覺,(住在郊區,樹比房子多,房間比人多。)多少長春藤,多少橄欖枝,多少三更燈火五更鐘,修得此身。
多少傾軋鬥爭俯仰浮沈,多少忠心耿耿淚汗淋淋,多少酒精大麻車禍槍擊,剩得此身。拚打趁年華,愛拚才會贏,不贏也得拚,一直拚到他從這個升降梯上滾下去,或 者從這些人的頭頂上飛過去。我也曾到華爾街看人,只見地下堡壘一座,外面打掃得乾淨利落,鳥飛絕,人蹤滅。這裡才是堂堂正正的戰場,千軍萬馬,一鼓作氣。
九時大軍過後,商店還沒開門,這才發覺他們是早起的鳥兒。何時有暇,再來看他們倦鳥歸巢。
歸途遇雨,今年初聞雷聲。
二o一二年八月十一日,補記如下:
十一年前,九月士一日早晨,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機,以飛機作武器,撞向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,紐約市著名的地標起火燃燒,爆炸,倒坍,成為廢墟。……..這天早晨,三千多人死亡及失蹤,我當初以早起看鳥的心情結一面之緣的人,吉凶難卜,後悔沒再去看他們下班。
「在亞當的時代,天堂是家;在我們的時代,家是天堂。」
人的第一個「家」是母腹,宗教家說人的前世經驗可以帶到今生,教育家說人在母腹裡的經驗支配長大後的行為,人在這個「大後方」接受最初的裝備。
人在母腹裡的姿勢最舒適,環境最安全,全身被打擊的面積最小,重要的器官都保護起來。痛苦時我們採取的姿勢,睡眠時我們採取的姿勢,羅丹雕刻的「沉思者」也近乎這個姿勢。
人類的第一個「家」是女性建立的。
然後我們需要第二個家,於是有父母的愛和勇氣包圍在我們四周,他們的胸脯最溫暖,臂膀裡最安全。家是母腹放大,家是天堂的派出所,所以說「上帝不能親自照顧每一個人,所以創造了母親。」或者可以加添幾個字,他也創造了父親,父母各自代表上帝的這一面和另一面。
照小篆的寫法,「家」字屋頂下面還有牆,像舞臺拆去「第四面牆」那樣,露出裡面的「豕」,於是巴金借小說人物之口說,「家」是屋頂下面一窩豬!這句話很鋒利,成為名言,影響極大,基督教會頗受壓力,只得為「天家」另造一字,寶蓋下面一個「佳」字。巴金鼓吹革命,煽動青年走出家庭,參加無產階級大家庭,大破大立,六親不認。學者認為「豕」字代表家畜,代表居有定所,代表由畜牧進入農業。女子飼養家畜,代表這時有了婚姻制度。這第二個家也靠女性建立。
今天戶籍上的「家」指結婚生子,否則只算「共同生活戶」,一門出入。我們說家家戶戶,兩者大同而小異。這個生兒養女的家也是女性建立起來,嬰兒的哭聲是沙漠駝鈴,丟在客廳地毯上的玩具是人類的新石器時代,兒女是自己的回顧,青春期、反抗期、都有你已喪失的優點,也重複你犯過的錯誤。兒女是祖先再生,高祖子孫盡龍準,祖父曾祖父的腔調身段都可複製,賈母是老祖宗,寶玉是「小祖宗」,如此這般也許可以解釋中國人人為何偏愛親生。
房屋公司的銷售標語說:「家是人生最大的投資」,標語旁邊畫著一棟房子。這句話和巴金相反,但同樣出自廣告天才之手。「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,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,」有人說中國人喜歡造牆,真的嗎,怎麼歐洲也有城堡,印第安人也有 wall st. ,美國也用小洋房代表「美國夢」。阿姆斯壯在月球上說「回家真好」。他們不是愛牆,他們愛那子宮的樣式。
最後,我們會有第四個家,宇宙,蛋白包著蛋黃,子宮的樣式,天家。「必有童女,懷孕生子」,道成肉身,完成人的救贖,這第四個家也是女性建立的。
依宗教家的說法,我們都是旅行的人,人生如寄,古人有「寄寄園」,庭園暫時寄放在我的名下,「我」又暫時被寄放在世上。終有一天乘風歸去,瓊樓玉宇,別是一番溫暖。
「回家真好」,回到第四個家更好,我們的家又是天堂,亞當失去的、我們又得到了。人必須四個家都有,這一代中國人的悲劇是國太多、家太少。天國,天堂,天家,國太嚴重,堂太空洞,最好是天家。
餘波蕩漾…….
蘇北坡:「在亞當的時代,天堂是家;在我們的時代,家是天堂。」好句子!何以沒註明是誰說的?
十二姨:很多格言都失掉出處,「失敗是成功之母」是誰說的?
楊揚洋洋:水果摘下來,忘了是那棵樹,也不想知道種樹的人,這是人性忘恩的証明。
寧為女人:甚麼年代了?還把女人定位在生兒養女?
十二姨:這篇文章的主題是「家」,用小品體裁,總不能把花木蘭、居里夫人、南丁格爾、德蕾莎修女都寫進去吧?
蘇北坡:我也來咬文嚼字,「寧為女人」,這個「寧」字透露了多少不得已不甘心,哈哈!得罪了!
江上風:我讀這篇文章,想起「君子之道,造端乎夫婦,及其至也,察乎天地。」寫得好!
十二姨:不要被意識型態遮蓋了文學趣味。
選文試讀:(二)「南京大屠殺」三段論
「南京大屠殺」,靜聽百家爭鳴,想到這個重大的慘案至今有了三個面目。
第一,抗戰文宣中的大屠殺。文宣的手段是訴諸愛國心和敵愾心,目的在激起報仇雪恨的義憤,情緒掛帥,立場至上。要知道那時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到處任意殺害無辜,人人親眼所見親耳所聞,跟全部人命總數相比,南京一地其小焉者也,經驗主義壓倒証據主義,數字究竟多少並不重要,宣傳效果百分之百成功。
第二,戰爭結束以後,出現了歷史記述中的大屠殺。史家講究史學方法,歷史著述須符合專業標準,它的手段和目的另有不同,以致衍化出「南京大屠殺」和「南京屠殺」兩個觀念。某些日本人以此為借口,堅持沒有南京大屠殺,請注意那個「大」字,至於「屠殺」,一般日本人的心目中還是存在的。
南京大屠殺究竟有多「大」?答案是三十四萬人。南京屠殺又究竟有多「小」?據說根據現有的資料,大約三萬多人。這九倍的差距怎麼辦?咱們政府戰後沒有認真調查,而今去日苦多,已是一籌莫展。抗戰八年,國民政府連自己的士兵戰死了多少都沒有準確的數字,何況老百姓!更何况敵人佔領區的老百姓?
國民政府以南京大屠殺概括戰爭時期敵軍的全面殺戮,又以局部証據概括南京的全部殺戮,多年反復爭辯造成一種印象,好像日軍只在南京一地殺人,而所殺的人數並不很多,這真是弄巧成拙!怎麼辦呢,有心人想到拍電影,這似乎是一個補救的辦法,電影是藝術,藝術可以「局部代全體」,藝術能使人感同身受、不求甚解,歷史沉睡電影醒,也許死結賴巧手而解。
電影拍出來了,可惜觀眾很少,新聞報導說,有些電影院臨時輟演,因為沒有人買票。如此這般產生第三個問題,電影裡的南京大屠殺該是甚麼樣子?電影講求電影語言,電影美學,藝術境界,恐怕還得有迴腸蕩氣的故事,視聽之娛的穿插,僅僅標榜真材實料,那是歷史觀念,反復宣示「凡是愛國的中國人都應該去看」,那是文宣觀念,電影藝術既有異於文宣也有別於歷史。
一九九年年底,美國<時代周刊>登出一篇文章,列舉二十世紀的各項特徵,其中一項竟是大屠殺流行!我想到當年有一種思潮,為了推動世界進步,一部份人(精英)有權消滅另一部份人(劣等份子),因此可以理直氣壯殘殺異己,何止一個日本軍閥放手蠻幹!時至今日,受害族群之中好像只有猶太人作出了成功的回應?
我們多少人好像還沈醉在抗戰文宣的效果之中,使酒駡座,向電影觀眾要愛國心,多少人明知債主已銷毀了貸款的憑証,卻主張欠債的人自動歸還,向日本政府要道德。多少人要求下一代爭氣、成器、將來以強制弱,討回公道,向子孫要補償。可有人討論:對這個不加引號的南京大屠殺,我們如何向全人類的後代作有效的轉述?如果我們僅有抗戰文宣的思維,斷簡殘編的史料,血淋淋的紀錄片?
補足歷史記述有待發現新的史料,要等奇蹟。化全民記憶為藝術,創造經典之作,風靡當代,留傳久遠,要靠天才。我不祈求「河出圖、洛出書」,只希望發現<安妮日記>、<揚州十日記>。我不尋找救世主、真龍天子,只希望知道誰是斯蒂芬·斯皮爾伯格(辛德勒名單導演)。歷史不容你不信,電影不由你不看,如此這般大屠殺才會成為鎔鑄國魂的原料,才有向世界控訴的喉舌。
選文試讀:(三)記者與作家
七七抗戰發生以前,中國的青年人有朝氣,肯上進。那時有個說法,青年最認同的形象是:黃埔軍校學生,新聞記者,土木工程師,外科醫生。(那時一般人認為中醫長於內科拙於外科,亟須西醫補救,合格的西醫為稀有傑出的人才。)
那時的新聞記者大概穿深色的中山裝,胸前左上的口袋裡插著「金星牌」自來水鋼筆,傳說他的那枝筆有魔力,他寫下誰的名字誰頭疼發燒。那時 的工程師穿工人的粗布服裝,大手大腳,時常從口袋裡掏出計算尺來東量西量,據說他的這把尺能量出來地球多大。外科醫生給人的強烈印象是戴口罩和橡皮手套, 那時沒有塑膠,大家說他殺人不用償命,因為沒留指紋。那時黃埔軍校的學生還鄉探親,只見他穿黃呢軍服,戴白手套,天子門生,鐵打的少尉,紮武裝帶,佩短 劍,他用那把劍殺人不償命,因為他殺的是敵人。
新聞記者布衣傲王侯,見官大一級。新聞記者總是飯局不斷,「和尚吃十方,記者吃十一方,和尚也要招待記者」。有一老兵說,抗戰 八年,道路流離,他看見多少人挨餓,新聞記者總有人供應三餐,所以他後來把女兒嫁給記者。內戰時期,長春斷糧,官方說餓死十二萬人,野史說餓死三十萬人, 有錢的人拿一棟房子換一碗米,房子還有、米沒有了。除了達官,有三種人不會餓死,軍人,美女,新聞記者。
文藝沙龍找我來談說新聞記者和作家的因緣,我看兩者難分難解,有人做作家做不好去做記者,也有人做記者做得很好去做作家,失敗的作家有兩條路,做記者或做教員,成功的記者也有兩條路,做官或者做作家。報紙是記者的前方,作家的後方,文壇是記者的後方,作家的前方。大英百科全書有一個很長的名單介紹「作家記者」或「記者作家」,用詞顛倒中寓有褒貶,前者文學成就大於新聞建樹,後者似乎相反。
有些好記者也是好作家,在我心目中外國有海明威,馬克吐溫,蕭伯納,毛姆,約翰根室,莫拉維亞;中國有蕭軍,徐訏,蕭乾,張恨水,王藍,范長江,曹聚仁,南宮搏。還有梁啟超和于右任似乎可以入列,但是又未便高攀。
現在南京大學有「作家記者班」,廣東有「作家記者俱樂部」,網站有記者作家網,山東大學有文學新聞傳播學院,這些都顯示作家記者合流。新聞寫作的方式是否因此發生改變?記者越來越像作家、還是作家越來越像記者?這是新聞研究所的論文題目。
新聞記者不是容易做成的,他得有外向的肉體,內向的靈魂,他熱情勇敢,同時冷靜周密,兩個不同的靈魂裝在一個腔子裡。他是好人,懂得一切做壞事的方法,他不做壞事做好事,但是他為了做成一件好事往往要先做壞事,相反的特質,矛盾統一,稀有難得,上帝用特殊的材料造成的破格完人。
新聞記者天天遇挑戰,時時有壓力,他吃的是英雄飯,憑一身武藝,水裡來火裡去。他是一個「不能輸的人」,而勝利的果實很快就腐爛了,運動員拿到金牌,他的榮譽可以維持四年,報紙記者的勝利只有二十四小時,電視記者只有兩小時,廣播記者也許只有十分鐘。同行競爭,你死我活,聚光燈照在誰身上,誰立時成為箭垛,相識滿天下,忽然最孤獨,春天迎接挑戰,路上沒有蝴蝶,夏天迎接挑戰,樹上沒有葉子。
我在報社打工的時候社會新聞掛帥,在很大的程度上,社會新聞就是犯罪新聞,採訪社會新聞的記者是王牌、是紅人。我跟一位社會版的明星記者 鄰桌而坐,只見他每天挺胸抬頭出去,垂頭喪氣回來,他忽然發現人民的道德水準極高!天下太平無事,找不到兇殺、貪污、強姦、拐帶人口、捲款潛逃。一天沒有 獨家,他在採訪組貶值,一星期沒有頭條,他在老闆眼中貶值,一個月還不見驚世駭俗,他在同行中失去尊嚴。有一天這位明星記者喟然歎曰:「我去殺一個人,回來自己寫,他們誰也寫不過我。」記者身處此境,父子不能相救,兄弟不能相顧,夫妻同床異夢,同行都是冤家。他們羨慕作家,一同說故事,一同朗誦新作,切磋 琢磨,種種佳話美談。
一般而論,作家的工作很安全, 新聞記者卻上了「最危險的職業」排行榜,名次緊緊排在警察礦工之後,位居第三。(服兵役是權利義務,並非職業,所以軍人沒計算在內。)我喜歡恩尼派爾,他的風格至今留在我的作品裡,他在硫磺島戰役採訪時被日軍的狙擊手射死。二戰戰場留下的紀錄,有一次「十天內死了七名記者」,有一次「一顆砲彈炸死五名記者」。據保護記者協會發表的訊息,二○○三年全球有六十二名記者殉職,其中十五名死於伊拉克,單是四月八日這一天之內就有七名記者受傷,次年五月二十八日,伊拉克境內又有日本記者兩人死亡,六月十日,BBC記者一死一傷。二○○三這一年,全世界有一百三十三個記者被本國政府逮捕坐牢,還有許多記者因揭發 黑幕遭黑社會打傷。
我們恭維記者,當面稱他是名記者、大記者,周勻之在他的「記者生活雜憶」中自嘲,名記者是「有名字的記者」,大記者是「年紀大的記者」。名記者不易,大記者更難,腦筋快,膽子大,運氣好,一條新聞可以名滿天下,若要大格局,大氣派,恐怕百年難遇一人。
何謂大記者?一九五三年,好萊塢拍過一部電影叫 「羅馬假期」,奧黛麗赫本演一個年輕的公主,葛雷葛萊畢克演一個美國記者,情節不必細表,公主天真爛漫,沒有防人之心,記者推動事件發展,乘機「偷拍」了她許多照片,足可寫一篇轟動兩國的新聞,那樣記者可以得大名,公主的聲譽和王室的尊嚴卻要受到嚴重傷害。最後記者把照片送給公主做訪美紀念,他放棄了新聞報導,等於放棄了普立茲獎。人散劇終,葛雷葛萊畢克獨立大廳之內,導演用仰角給他拍了一個鏡頭,拔高他的形象。這時他是「大記者」,不是名記者。
何謂名記者?這裡有一個真實的故事。某年非洲某一地區大旱,赤地千里,某記者驅車經過災區,烈日當空,不見人煙,只有一個幼童坐在乾裂的 土地上,奄奄一息,旁邊站著一隻兀鷹,這隻以腐肉為食的猛禽顯然在等那孩子死亡,然後啄食。記者停車拍照,然後趕回辦公地點發稿,那張照片登在各國的報紙上,我也在中文報紙上看見了,孩子又黑又瘦,衣不蔽體,脖子已無力支持頭顱,兀鷹的體積幾乎比孩子還大,目光陰沉盯住孩子的身體,背景則是一望無垠寸草不生,誰能拍 到這樣一張照片也算曠世奇緣,那位記者的大名立刻傳遍世界。有人問他那孩子後來怎樣了?他不能答覆,這就是名記者而非大記者。
名記者是新聞的產物,大記者是文化的產物。
我是讀報長大的一代,後來有聽廣播長大的一代,然後有看電視長大的一代,上網長大的一代,上帝造人,媒體加工,代代人氣質不同。看人挑擔 不吃力,作家看記者,越看越有趣,見過幾位了不起的採訪記者,上天不拘一格降人才,亦俠亦儒亦梟雄,能耐天磨真好漢,惹得詩人說到今。他們的故事今天一言難盡,不堪回首,新聞媒體慘澹經營,記者耗盡青春打前鋒,不眠不休,患得患失。世事無常,英雄無覓,回想我們當年那些貪瞋痴都隨雨打風吹去,早知道隆中高 臥,省多少六出歧山。
我不想做記者,只想做作家,人壽保險費比較便宜。記者是熊掌,作家是魚,我一直坐在魚與熊掌之間左顧右盼。作家空間較大,有不朽的作家,合時的作家,受人崇拜的作家,崇拜別人的作家。作家也不拘一格,鏗鏗鏘鏘的作家,嘻嘻哈哈的作家,奇文共賞的作家,孤芳自賞的作家,不專心的作家,不後悔的作家。有人如此介紹我:「這是最有名的作家,」對方一怔:「哦?沒聽說過!」你沒聽見過的作家仍然是作家。
選文試讀:(四)盼望宗教合作的時代來臨
唐朝的吉瑣和武則天有過一段對話:一桶水,一堆土,會發生衝突嗎?不會。水加土和成一灘泥,泥中會發生衝突嗎?也不會。若是把泥拿來做一尊佛、一尊玉皇大帝呢?那就要發生衝突。
宗教衝突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,我們不做研究,沒有學問,借著吉瑣和武則天的這一段對話來引導思考,倒也化繁為簡。世人尊崇宗教,本來是為了解決人類共同的問題,但是宗教以「具象」接引信眾,重要的宗教都有自己獨特的具象,信眾進入具象以後,宗教家要你永久停留在裡面,反而把人類分化了!這樣也許能解決一家一姓的難題,不能解決(有時反而加重了)普天普世的難題。海外有人研究為何華僑不能團結,指出「宗教信仰」為原因之一。幾乎可以說,宗教已成為割裂人群、经營壁壘、妨礙大同的最後一個因素。
2001年9月11日,紐約兩棟摩天大廈轟然崩坍,造成三千多人傷亡和經濟上的嚴重損失,也預告了宗教衝突的無窮後患。美國總統布希立刻邀請各宗教領袖聚集一堂,為和平祈禱。第二年開始,紐約市長彭博在每年最後一天舉辦早餐祈禱會,邀請各宗教領袖參加。他們似乎覺知天下事無法依賴「一神」降福,各宗教必須異中求同,始而互相包容,繼而分工合作。
我想起1975年蔣介石先生在臺北逝世,依基督教儀式營葬,主持葬禮的周聯華牧師在祈禱之前加了一句「史無前例」的話:「請全國同胞各自向你們信奉的神禱告,為總統蔣公祈福」。這句話在基督教內引起軒然大波,卻也給了我許多啟發。我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氣,我開始覺知一教一派無法包辦人類的救贖,每一家宗教都尺有所短,寸有所長。受眾有機會作其他選擇,任何一教一派無權剝奪此一權利。
我聽說原始社會部落林立,各個部落都有自己的守護神,這個「神」只保佑自己一個部落,而且幫助這一個部落去消滅別的部落,那時候,各宗教之間當然互相敵視,互相咒詛。至今仍有一些宗教,只救某一個地方的人,或只救某一個種族的人,這是「部落的宗教」,信仰這種宗教的人是很可怕的。我猜社會進化宗教也進化,各宗教同在現代社會中相處,脫胎換骨,但原始經典裡的部落色彩、狹隘的民族主義還殘留在靈魂裡,他們把經文中的部落與部落解釋為今天的本國與外國,把經文中非我族類的外邦人解釋為異教徒和沒有信仰的人,以致殺機仍在,宿仇未解,有些教派仍然以有我無敵而後快,信教的人如果能回顧歷史,就知道這種心態是世界和平人類幸福的障礙。
萬事莫如和平急,我猜宗教對抗的時代應該結束了,我們需要宗教合作的時代。各宗教的經典文本和崇拜儀式不同,经典儀式之後之上的東西可能無異,大家各以自己的說法做法去做和別人一樣的事情。以佛教和基督教為例,成佛好比是你考上了哈佛大學,應該還有很多很多大專院校讓大家受高等教育,上天堂好比你住進了曼哈頓的高等公寓,應該還有很多很多住宅讓更多的人安身.佛教基督教有共同的弘誓大願,兩路分兵進咸陽,西醫治不好的病還有中醫,火車到不了的地方還有汽車,不能坐飛机的人可以坐郵輪.人類有了佛陀又有了基督,我看是好的。
我甚至認為對佛陀的信仰可以深化對基督的信仰,對基督的信仰可以強化對
佛陀的信仰。他們的信仰沒有冲突,他們是一個信仰兩種形式,形式為內容而存在,我們順著形式求內容,我們不停留在形式上忘記內容。
當然,任何一個宗教領袖都要謀求本教的延長和擴大,他無可避免要和別的宗教競爭。依我們已有的知識,競爭要「誇張自己的優點,攻擊對方的弱點」,任何一個傳道說法的人都力稱自己的信仰唯一正確,絕對有效。中醫看病還會說「你得去看西醫」,基督教傳道人決不能說「你去試試佛教」。這是他們的苦衷,我們可以理解,但是我認為這是可以改變的,他們吸引信眾穩定信仰還可以有更好的方法,培養宗教人才的學院應該增加新的課程。
很可能最大的障礙仍在經典內容,歷史在他們之間造成很深的鴻溝,各宗教的領袖都是往昔拒絕互相見面的人物,今天能夠坐在一起吃飯祈禱,也能在低層次的技術性的事務上合作,例如救災,這是很大的進展。但是經典中惟我獨尊、排斥異類的文字猶在,目前只是存而不論,「半部論語治天下」。如果埋藏起來的種子未死,隨時可能發穿破土,我擔心他們尚未覺知,他們好比是鋼琴手,提琴手,或者鼓手,誰也不該規定世界上只准學一種樂器,他們要合起來演奏交響樂。
聖嚴法師說過一句話:宗教經典中如有妨礙世界和平的文句,現在要重新作出詮釋。他這個意見很重要,可惜沒有得到重視。如所周如,基督教在舊約時代,上帝只救以色列人,「部落的宗教」色彩濃厚,但耶穌重新作出詮釋,「世人都是上帝的兒女,」都是救贖的對象,天家的成員,基督教進入新約時代,這才成為人類的宗教。
我還記得,耶穌本來有反抗的精神,他提出好幾個煽動性的口號,例如「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、不要怕他」。他的道路很窄。後來使徒保羅重新作出詮釋,他要教會「順從掌權的,因為權柄是上帝賜予的」,天地就寬廣了。宗教靠殉道者提高,靠妥協者推廣,保羅給妥協者尋找經典支特,對基督教的發展很有助益。
我還記得,當我少小在家之時,佛教對文學創作的看法完全是負面的,世上並沒有賈寶玉其人,你居然捏造出一百萬字來,這是妄語,這是口業,死後要下拔舌地獄。我從圖畫中看見拔舌地獄的景象,兩個惡鬼像拔河,罪人的舌頭拉得很長,根深蒂固,欲斷還連,罪人痛苦的面孔和惡鬼猙獰的面孔長期對峙。據說施耐庵的子孫都是啞吧,因為他寫小說。那時候寫文章的人有罪惡感。現在「人間佛教」的說法不同了,文學家,音樂家,美術家,能創造出好作品,都是福德,人生在世欣賞好的文藝作品,也是福報。我們聽了如逢大赦,如歸故鄉,覺得佛教很有親和力。
如所周知,佛教一向認為做人和成佛兩者方向不同,修行的人要割斷塵緣,甚至脫離社會,佛門大開可是門檻甚高。等到佛教的發展在近代社會中遭到瓶頸,這才重新作出詮釋,佛法在世間,人成即佛成,修行可以和世俗行業並行不悖,甚至相輔相成,大概除了開屠宰廠。以前佛門即是空門,灰身滅志,現在佛門是大企業,許多人才找到出路,信徒湧入,佛教乃有今日一時之盛。
在很大的程度上,信徒的信仰來自宗教家對經典的詮釋,一個基督徒他信靠的並非是聖經,而是某一派神學,神學是對聖經有系統的解釋。經典不能改,詮釋可以變,佛門說「用佛法解釋外道,外道也是佛法,用外道解釋佛法,佛法也是外道」。大法官解釋法律,有時等於立法。漢傳佛教有十宗,基督教新教有兩百多個教派,都是「詮釋」造成的,詮釋能造成分歧,也能造成融合,能造成戰爭,也能造成和平。
當然此事非同小可,恐怕要佛教再出一個釋迦,基督教再出一個基督。目前可以先從內部研究著手,希望那一個基金會列為工作重點,鼓勵「學士僧」研究,鼓勵神父研究,鼓勵大學研究所讀碩士博士的人研究,辦一個專門的刊物,發表他們的論文。目前宗教領袖們只要不批駁,不歧視,「看草生長就好」。
選文試讀:(五)世界貿易中心大樓看人
今天,我到世界貿易中心去看人。這棟著名的大樓一百一十層,四一七公尺高,八十四萬平方公尺的辦公空間,可以容納五萬人辦公。樓高,薪水高,社會地位也高,生活品味也高?這裡給商家和觀光採購者留下八萬人的容積,可有誰專誠來看看那些高人?
早晨八時,我站在由地鐵站進大樓入口的地方,他們的必經之路,靜心守候。起初冷泠清清,電燈明亮,曉風殘月的滋味。時候到了,一排一排頭顱從電動升降梯裡冒上來,露出上身,露出全身,前排走上來,緊接著後排,彷彿工廠生產線上的作業,一絲不茍。
早上八點到九點,正是公共交通的尖鋒時刻。貿易中心是地鐵的大站,我守在乘客最多的R站和E站入口,車每三分鐘一班,每班車約有五百人到七百人走上來,搭乘 電梯,散入大樓各層辦公室。世貿中心共有九十五座電梯,坐電梯也有一個複雜的路線圖,一個外來的游客尋找電梯,不啻進入一座迷宮。
這些上班族個個穿黑色外衣,露出雪白的衣領,密集前進,碎步如飛,分秒必爭,無人可以遲到,也無人願意到得太早。黑壓壓,靜悄悄,走得快,腳步聲也輕。這是資本家的雄師,攻城掠地,這是資本主義的齒輪,造人造世界。是甚麼樣的模型、甚麼樣的壓力、使他們整齊劃一,不約而同?
我仔細看這些職場的佼佼者,美國夢的夢游者,頭部隱隱有朝氣形成的光圈,眼神近乎傲慢,可是又略顯驚慌,不知道是怕遲到?怕裁員?還是怕別人擠到他前面去?如果有董事長,他的頭髮應該白了,如果有總經理,他的小腹應 該鼓起來,沒有,個個正當盛年,都是配置在第一線的精兵,他們在向我詮釋白領的定義,向第三世界來者展示上流文化的表象。
我能分辨中國人、韓國人、日本人,不能分辨盎格魯撒克遜人、雅利安人、猶太人,正如他們能夠分辨俄國人、德國人,不能分辨廣東人、山東人。現在我更覺得他們的差別 極小,密閉的辦公室,常年受慘白的日光燈浸泡黃,皮膚彷彿褪色泛白,黑皮膚也好像上了一層淺淺的粙子。究竟是他們互相同化了、還是誰異化了他們?
這些人號稱在天上辦公,(高樓齊雲,辦公桌旁準備一把雨傘,下班時先打電話問地面下雨了沒有。)在地底下走路,(乘坐地鐵,穿隧而行。)在樹林裡睡覺,(住在郊區,樹比房子多,房間比人多。)多少長春藤,多少橄欖枝,多少三更燈火五更鐘,修得此身。
多少傾軋鬥爭俯仰浮沈,多少忠心耿耿淚汗淋淋,多少酒精大麻車禍槍擊,剩得此身。拚打趁年華,愛拚才會贏,不贏也得拚,一直拚到他從這個升降梯上滾下去,或 者從這些人的頭頂上飛過去。我也曾到華爾街看人,只見地下堡壘一座,外面打掃得乾淨利落,鳥飛絕,人蹤滅。這裡才是堂堂正正的戰場,千軍萬馬,一鼓作氣。
九時大軍過後,商店還沒開門,這才發覺他們是早起的鳥兒。何時有暇,再來看他們倦鳥歸巢。
歸途遇雨,今年初聞雷聲。
二o一二年八月十一日,補記如下:
十一年前,九月士一日早晨,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機,以飛機作武器,撞向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,紐約市著名的地標起火燃燒,爆炸,倒坍,成為廢墟。……..這天早晨,三千多人死亡及失蹤,我當初以早起看鳥的心情結一面之緣的人,吉凶難卜,後悔沒再去看他們下班。